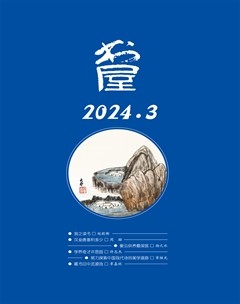一、侦探的故事
父母都是文科,父亲出身中文系,母亲外语系教英文,家中自然会有几大书橱的小说,理工类图书却一本也没有。当然我也就近水楼台,将书橱里的小说读了个遍,尤其是翻译小说。记得有一阵特喜欢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及霍桑的《红字》,在我的感觉中,前者是蓝银色,冰雪般的清澈,后者是暗红色,深邃而阴郁,两佳作正处于色彩光谱的两端。
母亲的好友陆慧英,单身未婚,是数学系老师,觉得我“尚可救药”,想尽办法让我离开文科是非之地,“弃暗投明”,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可我不知好歹“搭架子”,死缠硬磨就是不从,觉得数学太枯燥。再说学数学也得有好的基因啊,父亲这边好像还理性“尚存”,我母亲却是情绪的化身,还常回忆说她上中学时最怕数学老师,但一到上午十点钟的数学课,便昏昏欲睡,越怕越发困,无可救药,也不知最后是怎么混过关的。
不过陆阿姨的“策反”还是有潜在效果的,进了华师大二附中遇到的数学老师李绍宗,让我彻底改弦更张,迷上了数学。李老师是位极佳的数学老师,尤其是他逻辑极强,讲起课来势如破竹,一气呵成,条理分明,无懈可击,顿时让我“臣服”了。让李老师满意,似乎成了大家共同的潜意识。我至今记得李老师给我推荐了《正定理和逆定理》一书,让我获益匪浅。
其实李老师最得意的门生是另一班的女同学金成,绝对的数学头脑,且文理双全,常常指出“高观点”的重要性,比如代数即是在更高观点上对算术的审视和发展,于我可说是醍醐灌顶。不过阴差阳错,在初中唯一的一次数学竞赛中,居然让我夺冠了。其实竞赛的最后一题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但不知咋的,硬是让我连蒙带猜做了出来,大概是会点乐器的“小聪明”,在紧要关头,开了一下我的“脑洞”。不过老天爷是公平的,不会总让你走运抽上上签的,果然此后一直不太顺,虽说高中考入了上海中学,却在1966年成了最后一届“全须全尾”的高三毕业生。
日转星移,一晃“换了人间”。“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发小们常自哀自怜,叹道“生不逢时,可惜了”,都以为原本是会有所建树的。当然对我“沦为”小提琴老师尤觉吃惊。不过我却丝毫也不觉得“怀才不遇”,反而是暗自庆幸,没有“春蚕到死丝方尽”地献身于科学,大冷天龟缩在六平方米的小屋中苦思冥想的画面,怎么也让人羡慕不起来。更何况缺了谁地球不照样转,何必自作多情去做个苦行者。再说我有搞科学的才能吗,是这块料吗?我对此严重怀疑。我可能是一时兴起,依我一身懒骨,在最后临门一脚前保不定会“突然失去兴趣”,哲人般怀疑起人生来了。记得我的罗马尼亚小提琴教授就曾这样一针见血地评价我的一次演奏会。
虽然最终与“天时地利人和”一概无缘,逼得我辈“浪子回头”了,但中学六年对科学的兴趣还是在我身上打下了烙印,什么数学定理、物理方程式、化学元素表,早已扔到爪哇国去了,但有一件东西却是多年来一直如潜意识般如影随形,那便是“侦探的故事”,讲这个故事的不仅有柯南·道尔,更有史诗级的爱因斯坦。
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认为:人的大脑就像是个小阁楼,无用的东西装多了,有用的东西便装不下了。这个聪明的信条,正中下怀,成了我心安理得“摆懒”的座右铭。福尔摩斯的大脑袋尚且“寸土寸金”,何况我们的小阁楼?人得有自知之明啊!比如我是绝不会去观看电视知识竞赛,更不用说死记秦始皇年表去参赛了。相比虚构的福尔摩斯,爱因斯坦更是我们中学生心中的偶像,当然,也有同学口出狂言:“爱因斯坦为什么不能批判?”只能当作笑料,此乃横扫一切的“流行性精神病”,与正常人类无关。爱因斯坦语出惊人,开创了人类智慧的新纪元,“时间是相对的”“时空是会扭曲的”,这些观点实在是太震撼了,一如抓起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完全超出了“高观点”的范畴,常人是打死都想不出的!难怪说世界上只有十个人能读懂相对论,能作为潜在读懂的第十一人加入“相对论俱乐部”已成了我们的雄心壮志,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痴心妄想。
爱因斯坦似乎也知道我们赤脚也赶不上,望尘莫及只能干瞪眼的苦衷,便与另一作者合写了一本不厚的册子,专让尔等尝尝味道,入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