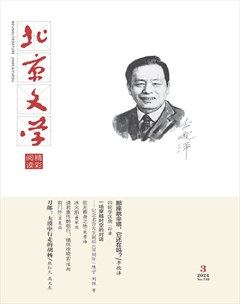住在北京郊区的米乐夫妇为让孩子在东城区上学,七年前怀孕时就开始布局,等到孩子顺利入学,又想出买辆房车来代替学区房的主意……这个看似周全的计划背后,“潜伏”着米乐对生活的“野心”,可房车能带着他和孩子逃离“内卷”的课堂,奔向自由歌唱的草原吗?
1
刚开始没想到是吃麻辣烫的,太饿了,从外面看着像能吃饭的地方,米乐和老婆便推门往里走。一进来,就想打喷嚏,呛得又打不出来。空气中,一个个香辣分子在翻滚。老婆一屁股坐到桌前,顾不得味道沾在衣服上将久久不散,扒拉着挑选。坐下后米乐意识到,他俩好久没有面对面坐下、像谈恋爱时候那样吃顿饭了。
店开在胡同口,狭长的桌子,其实也不长,顶多四五米;当中间儿掏空,擩进去一溜长方形钢筋锅,彼此靠钢板隔开,做成两排,煮着穿好的串儿,荤素都有,五花八门,竹签冲外,伸手即取。这种店傍晚前做旁边学校中学生和逛胡同游客的生意,现在已经晚上九点多,除了看店伙计在墙角刷手机,店里没别人,是另一种缘分让米乐和他媳妇坐到了这里。
两人各守一锅,小火轻煮,空调吹出冷气,汽化的风肉眼可见。老婆一言不发地吃着,面前摆着撸下的签子,长短不一。长签三块一串,短签两块——米乐发觉自己扫一眼桌面大概就能乘出吃了多少钱的能力退化了。两人都太累了,下午来这边看房,东跑西颠,看了六套,快看吐了。
九月份孩子就要上小学了,还有一个多月。目前孩子跟着他俩住回龙观,幼儿园也是这边上的,家楼下。老婆觉得,幼儿园哪儿上无所谓,就当上着玩,小学不能再凑合,必须去城里。回龙观属于昌平,挨着朝阳和海淀,算不上远郊,但比起二环里的东城西城,叫城外也不为过,这边都快到六环了。什么时代的人都想当“城里人”,过腻城里日子往城外搬的那种另说,家长更是希望自己的娃能做个“城里孩子”,恰好米乐老婆和孩子的户口在城里,进城上学成了这个家庭的不二之选。
当然米乐也有别的想法,他不认为孩子去城里上学就高枕无忧。他敢这么认为是有充分依据的,他的小学到高中都是在西城区上的,也不是班里所有人都考上大学了,甚至有后来进了工读学校的,前途如何,更靠孩子自己。同样他也不觉得留在昌平上学就输在了起跑线上,他的大学同学里,有一个就是昌平考上来的,学号一号,因为入校分数最高,后来年年领奖学金,还保了研。但米乐不愿跟老婆掰扯这些,他的不做主性格,让老婆成了当家的人。
说起来,其实他老婆连原汁原味的北京人都算不上,米乐才是北京的“城里人”。小时候在西城长大,家住西四胡同,后来那片拆了,父母在回龙观买了房,米乐跟着搬了家。户口随房子走,迁到了昌平,化身“城外人”。而他老婆,大学毕业留了京,幸运地进了给解决户口的单位,单位在东城,于是不仅成为新北京人,还拥有了令很多城外北京人羡慕的东城区户口,只不过是集体户。后来两人认识,结了婚,也在回龍观买了房——为了离米乐父母近,更因为这里的房价还能接受——老婆仍把户口留在单位。一开始米乐以为老婆嫌麻烦,懒得挪,直到几年后生了娃,给孩子上户口的时候,才弄明白老婆的良苦用心:孩子户口不在昌平上,上东城的,跟她一起,落集体户,将来是东城学籍,可以上东城的学校。大家普遍认为北京的好学校都在东、西城和海淀,所以这三个区的学籍格外珍贵,没有的心向往之,想辙往里钻,有学籍的则沾沾自喜不形于色。还有个插曲,备孕期间,老婆让米乐把他名下那套回龙观的房子卖掉,她研究过政策,必须父母双方都没有北京房产,孩子才能落集体户。就这么着,米乐把自己名下的那套房子卖了,租了两年房子,等到孩子在集体户里有了自己的户口页,才和老婆又在他父母的那个小区买了套二手房。那时候房价每年都在涨,为了孩子的户口,搭进去两人多年的积蓄,只因为老婆认为当个“城里人”洋气。
老婆七年前布好局,事态按预期发展着,上礼拜小学录取通知书下来了。儿子成了一名北京东城区的小学生,不出意外,将在东城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从回龙观到这所小学,二十公里出头,还有一段高速。不走高速的话,有三十三个红绿灯,早晚高峰开车少说要一个半小时,再遇上一起交通事故,时间就没谱了——若事故双方都是送孩子的家长,也是有麻利儿解决的可能。走高速倒是能避开些红绿灯,但进出高速口的时间不稳定,赶上没装ETC的车或手机忘带了无法扫码付费、身上也无现金的车主,这条车道何时能通车就看他什么时候能变出过路费了……这些特殊情况暂且放置一旁,按八点到校计算,逆推,六点二十必须出家门了,刨去洗漱吃饭时间,不到六点就得起床,大人还要伺候孩子穿衣吃饭,只能起得更早。于是问题来了:住昌平的儿童和家长,每日该如何不这般辛劳地去东城上学?
老婆曾试想,卖了回龙观的房,在学校旁边买一套,然后把自己和孩子的户口从集体户里迁出来,落户东城,一劳永逸;米乐乐意的话,户口也能从父母的本儿上挪过来,四十岁了,早该独立出来了。想法很美好,现实被低估。同样新旧的房子,东城一平方的单价差不多是昌平的三倍。现在米乐一家三口住的是一百二十平方的小三居,换成东城同档次的房子,包括税费里里外外都算上,要添八百万。知难而退,老婆降低预期,不行就住老破小,窄点儿也认了,孩子的教育胜于一切。看了两套不到八十平的两居,一算差价,仍要添三百万。钱是一方面,关键是卖了自己住得顺心又舒服的房子,在陌生的地方买个不那么如意的房子,是不是风险有些大?没有哪个普通家庭能在买房卖房上像打麻将出牌那般随意,即便是在北京,也尤其是在北京。
加之房产市场突然低迷,房价走向扑朔迷离,成交周期变长,房子也不是说卖就能卖成的,肯花钱倒是容易买到,但很可能刚买到手就贬值。如此一来,换房的想法只能搁置。保险一些的做法是把自家房租出去,在学校旁边租套房。今天看的这些出租房,有中介联系的,也有老婆在闲鱼找到业主直租的。看房用眼睛看,身体和情感不免也会参与其中,幻想未来至少六年带着孩子生活在这里:三副肉身的安放是否恰当合理(卧室舒不舒服),三张嘴能否被满足(厨房能不能焕发烹饪食物的热情),三个灵魂栖居于此可否相安无事(几年后将迎来儿子的叛逆期)……六套看下来,身心俱疲。
小店墙上的货柜摆着各种饮料,老婆偏偏拿了一瓶紅牛,拉开就喝。以前她从不碰这玩意儿,认为所谓的提神就是杀鸡取卵,把体内残存的能量榨取出来。那么,现在她是要把仅剩的一丝力气逼出来,然后还要干点儿什么吗?米乐猜不出老婆接下来还想干什么——再看一套房?或是仅仅为了有力气回家?还是不甘回家后就这样一无所获地睡去,夜深人静的时候仍要展开人生思考?
眼前的事实,让米乐确信了一件事情,这是近八年里他和老婆第一次吃麻辣烫。以前她特好这口,自打有了孩子,两人吃东西就不怎么考虑自己了,只吃适合孩子吃的东西,孩子现在六岁半,加上备孕和怀孕的时间,八年里两人渐渐没了“自己”。
此刻老婆两眼直愣愣地盯着锅里,嘴里机械地嚼着,一手握着红牛,一手搓捻着空签子,显然脑子里琢磨着什么。这神态让米乐陌生。老婆从小聪慧灵敏,在学习、考试、就业、升职的道路上,向来无须大动干戈便攻城拔寨,不说硕果累累,至少是一帆风顺。如今被卡住了,不是主观世界被难住的卡,是那种物质世界的卡——老婆想的可能是:自己的家庭为什么突然卡在底层中产向高阶中产进军的路上?
在不添钱的情况下,回龙观的房租只能在东城区租个六十平的老破小。客厅小得转不过身,家里那台75英寸电视搬过来都放不下——米乐和老婆都喜欢周末在家看个电影。为了让电视有地儿放,也得租个面积大的房子,那就只能添钱。添多少合适?无限制地添,好房子有的是,再大的电视也能搁进去,但这不是米乐家能过的日子。老婆虽说事业顺利,挣的也有限,在出版社上班,不是什么大社,做出爆款书的机率渺茫,年薪远没到过日子可以不算计。米乐至今自由职业,做平面设计,收入取决于活儿多活儿少,曾经红火过,这两年客户相继流失,不知道好好的一家公司怎么就做不下去了。米乐的活儿也随之减少,世界越来越新,他越来越老,在发展新客户上缺乏手段,已由只喝单一麦芽改为调和威士忌也觉得还不错了。
老婆定了一个标准:保证生活品质的情况下,房租尽可能地少添。尽可能地少,也有一个范围,所以连看了六套。连将将满意的都没有,首先就是感觉小。房子住惯了宽敞的,再换紧凑的就难了。米乐老婆以前没觉得三口人住五十多平有多挤,甚至还觉得敞亮,她自己家当初就是一套五十多平的房子,她还有一个自己的房间,让很多同学羡慕,但那是二十多年前。现在她和米乐看了一套九十平的两居都觉得窄,就这还要每月添四千多;若想租一套和回龙观的家一样面积的房子,少说要补八千块,超标了。也正应了那句话:一分钱一分货。越活越觉得这话的准,世界就是这么构成的。
六套里有一处平房令米乐夫妇印象深刻,房本面积三十多,号称能住五口人,两间十余平的房子打通了,加了挑高,做成复式,下面的三十多平隔出客厅、厨房和卫生间,客厅只留一条过道能站直身子,其余空间留给楼上复式,从沙发上起身都得猫腰。房主说,人多数时候在客厅里是坐着的,这么设计是合理利用顶部空间。楼上的复式部分,拆分成两间半,老两口一间,中年夫妇一间,半间留给上中学的孙子住。现在孙子考上大学,可以住校了,一家人没有必要挤在这里,准备往城外搬。看房的时候,米乐老婆盘算如果是自己家搬过来,先不说人能不能耍得开,就是家具都摆不下。这家的柜子有个特点,都直通房顶,极尽盛放之能事。经过楼梯的时候,米乐老婆不知道自己碰了哪里,一扇木板弹出来。原来这片看似楼梯支撑物的木板也是柜门,楼梯下面的空间从高到低依次被用作大衣柜、短衣柜、袜子柜和杂物柜,房间里见不得一立方厘米的浪费。连柜门上都没有把手儿,门是磁吸的,按下去则弹开,再按就吸上,刚才就是米乐老婆不小心顶到柜门。房主人笑着介绍说,面儿上什么都不露,省地儿。笑中透着说不上是得意还是无奈。这一刻,米乐老婆体会到住城外的好了。
但米乐知道,对老婆来说,东城学籍是更好的东西。现在终于等来这一刻——媳妇累了、也烦了的时刻——他可以把存在心中许久的那个想法说出来了。
“倒是还有个方案……”米乐不知为何话一出口感到一阵心虚。
“什么方案?”老婆翻起不抱希望的眼睛。
“弄辆房车。”
“现在卡在房子上,怎么还想着弄什么车!”老婆似乎觉得米乐把握不住重点,随后马上意识到房车是可以住人的,转而说,“弄了以后呢?”
2
大学毕业离校那天,米乐想,以后可他妈的不用考试了。这么一想,步伐都轻盈了。现在四十岁,竟遭遇了哈姆雷特的困境:孩子的小学到底是去东城上,还是留在昌平?这道题没有补考,选错了就……就怎样并不知道,也没有人能告诉他。
做这同一道题,米乐和老婆的解题思路不一样。不同于老婆在跨城中寻求解决方案,米乐是先有方案,然后为这个方案在现实生活中找到有力支撑。方案就是他跟老婆所说的“弄辆房车”,直觉告诉他可以这样做。
米乐现在和父母住同一个小区,隔着几栋楼,相互都有个照应。幼儿园接送孩子,当米乐和老婆顾不上的时候,他父母可以代劳。老两口把孩子接回来,还能给孩子弄口饭,米乐他俩几点回家都无所谓了,孩子睡爷爷奶奶那儿也行,第二天老两口再给送去幼儿园。父母眼瞅着奔七十了,不是这个今天头晕,就是那个明天胸闷,米乐也能照顾到,去医院检查他开车接送方便。所以他不想打破现状,觉得孩子小学在家附近上也没什么,父母依然可以帮着接送。但老婆的底线是,别的怎么都行,学必须去东城上——尽当爹妈的最大努力成全孩子。因为她就是这么长大的,然后从一个四线城市考到北京,当初她妈不输孟母,为了她上学,也曾三迁。
让孩子住学校旁边,已是大势所趋,在这个“规定动作”下,米乐便想到了房车。他一直就想弄辆房车,可以开到哪儿玩到哪儿,需要工作了——他的工作有台笔记本电脑就能完成——车里就能干。有卡座和桌子,不比咖啡厅差,窗外还有风景。可以说,是孩子上学的新问题,正好撞上他的旧心愿。
然后今天看完房子,也可以说在看房过程中,甚至说在第一套老破小看到一半的时候,“时机到了”的想法就开始在米乐脑子里闪现。他想,与其在“砖窝”里睡觉,还不如在“铁桶”里睡,反正都是个小。不就是为了离学校近吗,把房车停学校门口,没有比这更近的睡觉的地方了。相当于给小平房装上轱辘。每天放学先开着房车接孩子回家,小学特别是低年级,三点多就放学,这时候路上不堵,四十多分钟就能到家。在家写完作业吃完饭,玩够了,该睡觉的时候,就让孩子往房车上一躺,米乐把车开到学校门口——晚上不堵车,四十分钟用不了就能开到。孩子瓷瓷实实睡一晚上,米乐早起给孩子做饭,车上有电磁炉和冰箱,孩子妈愿意陪睡陪吃也行,车里三张床,足够睡下,比那复式平房的卧室,更让人有想躺在枕头上的愿望。
如果是搬来东城,米乐不忍心只搬自己的小家,而把父母留在回龙观。这样一来,不仅开销翻倍,父母也得挤老破小。现在老两口住着百十平的两居室,在一层,不用爬楼,关键是窗前还有个小院子。院子算公共面积里的,因为搬来得早,那时候物业管得不严,老爷子在落地窗前开了个门,直通小院,方便打理草木,省了物业的事儿,这地界儿慢慢也就算自己的了。进入四月,院里的那株树仿佛懂得感恩,不用催就按时开花,白中泛粉,围住树冠密密一团,阳光下尽情盛放。引来蜜蜂,路人也在树前拍照,老爷子坐在窗前泡茶,得意地看着外面。打开窗,风吹过,花瓣会飘进窗里——三四月还不必关窗纱。米乐爸会特意让花瓣就那么散落在窗前的茶几和藤椅背儿上,放那么几天,等花瓣蔫瘪了再扫走。花期一个月,落光后小绿果就冒出来,一周后能看出是杏。到了五月中,杏的个头儿大了,坠弯枝条,有人摘着吃。米乐爸爸看到会拦下,让他们捡掉在地上的吃,这种杏熟透了,不酸。自打搬进这套房子,米乐家就没在吃杏上花过钱。等杏的热乎气儿过了,轮到杏树旁的那些灌木展示,开出一大朵一大朵的花,红彤彤不免艳俗,绽放的热情仍让人忍不住问问这是什么花,很多时候米乐爸故意站在院子里,等着回答:月季。真要搬了家,在北京二环里找到一处窗前有杏树的房子就难了。这是米乐给“弄辆房车”找到的理论支持。
但老婆听完米乐的计划后,第一反应就是不靠谱,这也是她的直觉。完全在米乐预料中,她这些年越来越保守。米乐当然也理解,这种保守从某个角度说,是母爱所致,本质出于对孩子安全的考虑。但米乐这么做——如果房车计划能成行——也不是说就没有父爱了。恰恰这是米乐要传递的父爱,不要被生活中那些貌似坚固的东西困死,如果甘于受困,那些东西会越来越坚固。老婆的保守从另一个角度看,跟对房车的不了解也有关系。
米乐从技术角度给老婆普及了房车知识,告诉她里面床的尺寸,如何取暖、洗澡、做饭,以及一些先行者已经在房车里过上怎样的日子。说着打开手机,调出几条短视频,让老婆看人家怎么在车上过日子,有游荡在城市中的,也有开到荒郊野地一住就是个把月的。
老婆敏锐觉察到蹊跷:“你不是为了孩子上学,你准备了半天,是你想弄辆房车玩吧?”
米乐承认他是爱看那几个房车播主的视频,正是因为平时关注着,关键时候就用上了:“人家成年累月在车里生活,咱们就是让孩子睡个觉、吃个饭,比换房简单多了,风险也小。”
老婆随之问了几个她关心的问题,包括车得多少钱、车牌好不好上、冬天睡觉怎么办,以及米乐能确保每天晚上和早上都像他说的那样守着房车吗?米乐张口就答,新房车从十几万到上百万的都有,开了两三年的二手房车是新车的六到七折,他觉得买辆二手的就行,甲醛味儿散干净了,孩子睡在里面踏实。车牌可以用家里这辆车的,把现在这辆ix35卖掉,开八年了,孩子都长大了,没有上学这事儿,也该换辆大点儿的车。冬天则还在家里睡,可以提早一个小时出门,让孩子在车上洗漱吃早饭,早高峰之前赶到学校。最后米乐保证道:“既然我提出这个方案,我肯定不会缺席。”
“万一呢,万一你有事儿,或者出差不在北京?”老婆像一位象棋大师,考虑的不光是眼前这步,还有很多步。
“你也可以开,练练就行,C本以上都能开。”米乐不是留后手,是鼓励老婆,他觉得这是一次机会——把老婆从盲目内卷的势头里拽出来。让她除了惦记“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心里也装些别的事情进去,比如想想能开着房车去哪儿过个周末。
他早就对老婆的一些做法不认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