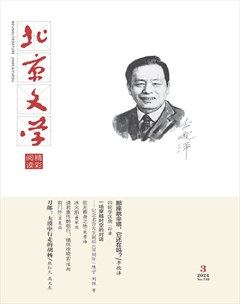激流群哮,海声浩荡,一道闪电在夜空中亮起来,将乌云撕成两半。一个社区医生被带到幽深的宅院,死亡的阴影降临,各路人等聚集于此只为审判宅院主人的命运,而社区医生也将在此完整地目睹一个人跌宕起伏的一生。
暮色浓重,但是在大地黑暗的底色之上,西天清朗的海空低处仍有一线暗红的残霞横亘在数条深灰色乌云之上。而在海空的另一边,不大一块浅褐的云丛中不时会亮一下白色的闪电。他头天到得晚,幸好房子是早就租好的,妻儿又暂时没随他一起来,一个人总归好办,按照那个貌似很急迫的合同约定,第二天一大早他就上了班。原先知道他要服务的是城市的一个边缘社区,没想到边缘得那么远,几乎就是远郊,也可以说就是乡下,因为在濒临大海的城市白色主调的建筑群和他签了十年工作合同的社区之间隔着面积广大的荒野,头一眼看上去竟给了他一种无边无际的深刻印象。荒野上植被茂密,林木葱郁,让人感到压抑,透不过气来,好在这荒蛮沉默的一片绿色海洋中到处开着花,赤橙黄绿青蓝紫,绚丽夺目,不是一般的有气势,与城市那边隐约可见的海有一拼。这类地方对于旅游者或者避世隐居者来说相当不错,空气清新,馥气四溢,离海不近也不远(最近的海湾据说只有十分钟车程,刚来第一天就要上班他当然没时间去看上一眼,而能够随时看海恰是他下决定抛弃北方某内陆省城三甲医院主任医师的工作到这座岛上做一名社区医生的原因之一)。只是社区就在这荒蛮广大的一片之中,居民住得分散——一色高档别墅小区,或是一栋别墅自成一区——社区医生却只有他一位,虽然去机场接他的社区主任告诉他,如果不够他们还会考虑为他再聘请一位助理,但话外之音他也听出来了,至少目前这个看起来和城市主体建筑群在海岸边的延伸线差不多等长的社区将只有他一名医生为辖区居民服务。服务的范围无所不包,岁数不大领导风格却显出强悍作风的社区主任却不想在这方面和他讨论,并在初次对话中就暗示说,他们答应跟他签那么高薪酬的合同时上面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了。谈话结束时,社区主任无意间还说了另一句话:
“本社区的居民同意聘请您来的条件之一,就是相信您能够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第一个白天情况尚好,很忙,但不知为何医生仍觉得没有想象中那么忙。黄昏时分下了几滴雨(这地方总是多雨的),之后又晴了。下班时间到,他给最后一个冒雨送上门来的年轻外伤患者缝了针,裹伤固定,又帮过了下班钟点才到的另一名老妇开了治便秘的药,是啊,全方位的服务,他想。因为仅有的一个护士兼司药也在休产假,他连她的工作也兼了。然后他又等了一会儿,才关门回到临时公寓里,胡乱泡了一包面——还是累,主要是头一天,有些紧张,不想下去到一条有村级吃食店的小街上找吃的,那里其实有些看上去还不错的乡村小店,连咖啡店都有——恰在他要把第一勺面送进口腔时手机铃声响了,接他紧急出诊的专车也到了楼下,甚至司机也直接跑上来,帮他提起出诊包,这次是要他出急诊。
一路上那辆一眼就看得出价值数百万的豪华商务车一直在比车顶还高的暗色植被中穿行,使他有一种出了门就一脚蓦然从白天跨过黄昏直接进入黑夜的沉重和不真实的印象。大風从海上强劲地吹来,路两边的暗色植被随风动荡起伏,车子如同航船在海浪中颠簸前行,让他不适,想呕吐又止住。好在患者所在小区到了,由一条半公里长的私有的直道与环岛公路相接,一座完全陌生的暗黑森林中的村庄出现在眼前,与那种如同连车带人沉入一片深水的窒息感极其吻合。村口已经站着不少人,奇怪的是他分明看到了路灯,却一盏都不亮,这些人在黑暗中像一些影子一样飘忽不定,若隐若现,同时又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分明是在议论着什么,看到车到了,便都住口,把面目转向他。医生下车,从他们中间走过,留意到自己还是错了,不是一座村庄,而是一座被汽车灯光短暂映亮的占地宽阔的独立住宅;这些人站立的地方也不是村庄的入口,而是这座大而无当的豪宅大门外的空地。豪宅的两扇大铜门半掩着,有一盏门灯却不亮,完全不可能从昏暗的夜气中照亮空地上那些模糊难辨的面孔,却让医生冷不丁地感觉到人群中暗藏或者正在酝酿着的某种越来越惊恐和歇斯底里的气氛。当然它们不过是些梦幻般的即来即逝的瞬间印象,医生这时想到的只可能是病人,可是从那些看不清面目的人影中他已经听到他们喊出的话语:
“是医生!医生来了!”
“快领进去,他就要死了!”
“别磨蹭了,你来晚了!”
“……”
医生跟随一名他其实并不知道身份的粗壮男人进了宅门,流水般的瞬间印象在继续:一时间他觉得这座宅门更气派了,简直是一座单独雄伟的建筑,高大、威严、现代,门前还有两尊汉白玉的狮子,一人多高,在夜气中张牙舞爪。随后他被粗壮男人引着经过一座天井式的庭院,几盏不大明亮的庭院灯让他难以看清其间的景物,他很快被接着迎上来的几个模糊的人影带进了豪宅的主体部分,一座占地豪阔的四层宫殿式主楼,并很快被单独领进了楼门,进门时他再次发觉头顶上仍然只亮着一盏灯,光线越发昏暗,灯光只照亮了门内一小块大理石雕花地面,其他空间都藏在户外流动的夜气般的阴暗中。他意识到一路从庭院真正随他走向主楼的人影越来越少,进门时除了那个壮汉,他仅仅注意到门灯光亮照不到的昏暗中,紧靠楼梯的地方,隐约闪过一个妙龄女子的影子,转瞬即逝,他没看清她的脸,能感觉到的只是她的衣香鬓影。接着他被壮汉匆匆带上了二楼,进入病人的房间——凭空间之大和装饰风格之豪奢他想到了这是主人的卧室——那个引他上楼的壮汉并没有进来,只是停在门外,抬手朝卧室深处一指,抛下一句话,转眼就不见了:
“他就在那里!你快去看看吧!”
医生发现只剩他一个人立在病人房间后很快就从初始的震惊中镇静下来。医生人过中年,小肚腩都有了,见过的世面不少,像许多他这个年龄的男人一样,现在也模糊地认为人生来到世上就是受惊吓的,然后你就有了资历,遇上什么事情也不会蒙圈了。他放下出诊包,故意慢条斯理地取出手套,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戴好,顺便粗枝大叶地留意了一下这间显然像豪宅的每一部分一样故意装修出某种夸张怪诞风格的宽大卧室,注意到在半圆形罗马柱、丘比特爱神小雕像、几幅敦煌壁画风格的天花板和壁布之外,一个靠窗的墙角上居然还立着一盏差不多杵到天花板上的落地灯,汉代墓葬出土的长信宫灯的形制,只是举灯的不是胡人而是一位脸上涂了两团胭脂面目诡异腰肢袅娜衣带飘飘的宫女。像整幢建筑内外一样,这间卧室的灯光也不亮,注意到这件事他才发觉整个房间居然只有这一盏宫女举灯亮着。医生试着在墙上寻找别的开关,想打开更多的灯,让房间更亮些,以便能看清楚病人。但是没用,他找不到开关,只能放弃,一边走近病床,一边将目光投向病人。后者仰卧在一张同样大得夸张的床上,身子被一床薄被子裹得很严,只露出了一个半老男子的面孔。他还是再次被惊到了,即使躺在这么大一张床上,病人的身躯仍显得高大伟岸,两只大脚也从被子里露出,几乎要伸出到床外去。那盏孤零零的宫女举灯的微弱光线并不能直接照到病人脸上。于是这张脸除了轮廓线条细部也显得模糊。医生久经战阵,在他的职业生涯里见惯了这样的脸,它们接近死亡,正在死亡,但仍没越过生死之阈。医生做了一个深呼吸,先弯腰伸手试了试病人的鼻息,然后按照职业程序动手检测这副一息尚存的生命躯壳目前的状态。最终让他魂飞魄散的一幕还是发生了:病人离他最近的一只大手刚才还毫无生命迹象,这时突然抽搐了一下,两根手指抓住他的手腕,医生觉得自己听到了一声来自地狱深处的近乎无声的叹息:
“帮帮我……”
只用短短五分钟医生就结束了自己的工作,手提出诊包离开了那间鬼气森森的卧室。走廊里一个人也没有,壮汉并没有在门外等他。他在昏暗中摸索着找到楼梯走下去,走向一扇半开的门,仍旧没有人,还是那盏昏黄的门前灯亮着。他出门,才看到壮汉和刚才在庭院里见过的几个黑影左左右右地向他跑来。“医生,他现在怎么样了?”有人问。医生什么也没说,匆匆走过庭院,这时跟上来的黑影由五六个增加到了七八个。没有人再问什么,大概他们都听到了第一个迎上去的人问他的话,并且也都觉察到了医生的缄默,有几个人就在医生走向的那座很气派的高大宅门后面停下了。医生感觉到他们里面有一个细瘦的影子很像方才他进入主楼后在灯光昏暗处模糊发现的年轻女子,后者只是远远地跟着那七八个黑影走了几步,并没有跟上来。
现在醫生走出了那座高大的宅门,站到了门前的台阶上,发现聚集到宅门前空地上的人影更多了,比他来到时增加了一倍还多。大风劲吹,空中有了一种暴雨将至的湿热气息,乌云全部遮没了天穹,四周围的树丛发出巨大的呼啸声。虽然如此,他站在这里仍觉得眼前比刚到时亮了一点儿,第一次注意到这座独立的、被林木和高大植被簇拥包围的豪宅大门外的空地面积有多么大,空地那一边还有可以停车的车场。除了已经麇集到这块空地上的人影,那些闪亮的车灯的光芒帮助他注意到正有更多的人和车陆续赶来,同时方才那一种惊恐、悲伤和歇斯底里的气氛也正随着更多人车的到来悄悄地被强化,它们如同一群沉默的野兽,暂时蛰伏在黑暗丛林的深处,还没有以一声突然的长嗥打破狂风、乌云、林木的啸叫,时间本身加给它们的谨慎与克制绷紧得如同一张膜一样薄的平静。但他的出门已经扰动了这张膜,原来还是三三两两一丛丛一簇簇站立的人形黑影忽然像昏暗的河流中滞留的团团漂浮物一样向他漂动过来,又像暴雨后激流中的漂浮物聚拢到河心岩石前一样在他身前聚拢,最终汇成黑压压的一片。他以为自己终于能看清这些人的脸了,但是诡谲的事情又发生了,豪宅大门前的唯一一盏灯突然熄灭,黑暗瞬间吞没了一切,包括那些他想看清的人的脸。他想到了躲开,但错过了机会,这些在黑暗中他仍然能模糊看到的人影从四面八方围住他,将他逼下了台阶,站到了空地上,他在这段他们向他聚拢包围的时间里听到了他们小声的嘈杂的音乐般多声部的话语,真正听清的却是这些话语中不连贯的单个的字和词,它们不是在表达这些字和词本身的确切含义,而是在通过它们表现自己参与到今晚这场令所有人猝不及防的聚集后的感受和要承担的情绪与压力,其中最不缺少的就是震惊、担忧、恐惧、悲伤,最不可理解的还有愤懑与怀疑,不愿意接受已经听到的信息。如果说他们就是夜气笼罩下的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这些情绪就是湍急的激流中的漂浮物。同时要越过阻拦住它们的河心的岩石,涌向它们暂时的目标,也就是医生,然后所有的漂浮物,不,情绪,又在同一瞬间化成了急切与焦虑的叫喊,冲着医生响起——
“你见到他了?他怎么样了?”
“不会是真的吧?”
“你快说呀!我们要知道真相!”
“……”
黑暗中这些模糊的人影还在越聚越多,不过仍算不上豪宅大门外空地上已经聚集的众多人影的全部,其他后到的人们离得太远,都溢到空地外的私家道路上去了,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暂时还没有意识到医生的出现,但这最先聚拢上来的一群也成了黑压压的一片,推拥着他在湍急的激流中移动。医生开始有了一种随时被他们卡住脖子陷入窒息的恐惧感。在这些黑影中他听到了男人们低沉、有力、喑哑、连呼吸带喘的强大声息,但更多的却是女人们多种声腔和情绪混杂在一起的急促的追问。当然是这样了,危机一旦发生,最沉不住气的总是她们,男人们无论为了尊严,还是天性如此,总会较为镇静,哪怕是故作的,也会比女人表现得稳重和矜持,虽然他们内心不见得真比女人更沉得住气。但是嘈杂的女声过了一会儿还是低下去,仿佛喊了很长时间后连她们也忽然明白了,医生一直保持的沉默只会在一片混乱中被某个听起来最具权威感的男声打破。
一个显然过了中年的男人的身影完整地出现在他面前,医生顿时觉得这是他今晚看到的第二个高大伟岸的男人,因为他的影子几乎遮没了他面前的全部夜空。
“你是医生?”他用一种很沧桑却仍旧有力的嗓音问道。
“是的。”医生终于开了腔。
全方位的服务——他又想到了这句话——是不是也包括向这些人服务。可他们真的全是本社区的居民吗?
“我们有问题要请教。”
“不用客气,你们想知道什么?”他不情愿——十分不情愿——地反问道。
“刚刚听说了他的事情……如果是真的,为什么不马上送市里去,干吗在家里拖着?”
医生想说什么,还没有出口,高大伟岸男人身边的又一群男女叫喊起来,并把前者挤到一边去:
“你只是个社区医生,你行吗?”
“快叫120吧!”
“难道要拖到他死吗?”
“……”
这些叫喊声像方才一样嘈杂,几乎淹没了豪宅周围林木的狂啸。医生重新恢复沉默。一时间他认为这也是他的权利。
“不要喊了,难道医生不比你专业?连医生都选择了不叫120,那就是说……”
嘈杂的男女声低下去,风声和林木的啸叫声重新在医生的耳边高亢宏大起来。
“那好吧,你就告诉我们,他怎么样?”过了一会儿,那个高大伟岸、极具权威感的男人的身影回到先前的位置上,再次开口道。
“不好。”虽然有继续沉默的权利,但这一次医生还是忍不住给了他和他们一个最简洁和肯定的回答。
“怎么不好?”又有人冲他喊,其中夹杂了更多女人的哭腔。
医生坚持自己的权利,继续用沉默回应这嘈杂的一群。
黑压压的一片恢复了安静。还是高大伟岸的男人,站稳自己的位置,想了一想才道:
“怎么不好?”
“我是医生。有职业操守的。未得到家属允许前,我不能泄露患者目前的状况以及不能叫120的原因。”医生用有点愤怒的声音道。
“我们就是家属。我是他唯一的妹妹。”一个女人忽然像条灵巧的鱼从鱼群中游出一样,从高大伟岸的男人身影后钻过来,站到他的面前。“这是我丈夫,”她回头模糊地指示了一下伟岸男人,回头向着医生,声音咄咄逼人,“我哥哥目前处在独身状态。我们听到消息第一时间就到了,可是不让我们进去看他。我们有权从你这里得到真实消息。”
医生朝她看一眼,夜气浓厚,近在咫尺他仍然看不清楚这个小个子半老女人的脸。虽然她的话说得气势逼人,让人无法置疑,但他仍然不能仅凭女人自己的这番话就相信她。他选择不理她,继续沉默。
“我太太确实是他唯一的妹妹。以他现在的婚姻状态,他的亲属除了我太太外就没有别人了。”高大伟岸的半老男人改用一种更耐心、也更斩钉截铁的声调道,试图说服医生,“你应当相信她的。”
医生只是看了看他——仍然看不清男人的脸——他继续沉默下去。
“那好,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也不用藏着掖着,这也不是藏着掖着的事儿。”咄咄逼人的小个子女人完全不耐烦了,又站到丈夫面前来,尖声冲医生发泄自己的愤懑并主张权利, “你就直接告诉我们,我哥哥自杀这件事是不是真的?人这会儿一定不在了,只有这种情况下你作为医生才会拒绝叫120把他送进城里急救是不是?……还有,他是服毒自杀,这个也必须确定,告诉我们,他是吗?还有下一个问题,这里面有没有刑事犯罪,有没有可能是他杀!”
又一道人影的激流向这片黑压压的人群奔涌而来,它们比刚才的任何一支激流都更有气势,几乎可以说以摧枯拉朽之力荡开了潴聚在它面前的人群之影,直接在医生面前停下。由于它的到来,就连刚才一直气势逼人地对医生说话的小个子女人和他身后的伟岸男人也很被动地让出了部分空间。
“你是医生?”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立即嘹亮地响起来。
“我是。”这次医生决定主动回答,他说。
“刚才有人在这里说她是他的唯一亲属,谁敢这么说话?要说唯一的亲属,我才是——我是他唯一的女儿!别人谁都不是,首先他自己就从不承认!”那女子四下环顾所有的人影,比刚才的小个子女人更加严厉、更气势逼人地说道。
“哎我说美丽,话可不能这么说。不管以前发生过啥事,到了今天这种时候,我总还是他的表妹,是你的亲表姑吧?再说了,我们又不是来这里争什么,我们只是听到消息,就最先赶了过来!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谁?”是小个子女人在说话,这会儿她又不是唯一的妹妹而成了表妹了,并且退到了高大伟岸丈夫的身后,气焰低下去不少。但接着悲伤来临,夜气里出现了哭泣的声音、擤鼻涕的声音,连同越来越不平的喘息。“你一个小孩子知道啥?要是没有我,就没有他的今天!你知道啥叫艰难?当年要不是我和你表姑父在最关键的时候借给他一笔钱,他头一家公司就开不成!所以我可以毫不隐瞒地告诉你,他的公司里有我们的份儿!”
“再说你妈妈也早跟他离婚了,你连姓都不随他的,公开声明和他断绝父女关系,不能算是他的闺女了吧?”年轻女子身后的人群中,一个男子突然恶毒地插话道。
年轻女子蓦然回头去寻找,当然她看不清说话人的脸,她连那人在什么位置也发现不了,但她的锋芒还是仿佛被那人挫伤了,瞬间整个人变得茫然不知所措,不过很快就缓过神儿来,怒不可遏,开始反唇相讥并哭泣:“我妈是和他离了婚,可这毕竟不能改变我是他女儿的事实!我那个声明是我妈违背我的意志发的,我根本不承认!说到底你们不全是为了他的财产继承来的吗?好吧,你们今天有一个算一个,都给我听着,只有我才是他财产的唯一继承人,该是我的就是我的,谁也甭想拿走我的东西!”最后,不知是不是觉得力尽词穷,她爆发式地大声号啕起来。
一个年轻男人的影子突然从后面挤开其他人影,冲过来将女子抱在怀里,大声道:
“亲爱的,别哭!我来了!我在这里,看谁敢欺负你!”
女子像是被毒虫蜇了一样,骤然不哭了,全身激烈发力,要甩开他,又回头啐那人一口,叫道:
“你给我滚!我爸出事了,你倒冒出来了,快回去找那个让你喜欢的婊子去!别缠着我!”
接下来更令人惊骇的事情发生了:那对刚才还和年轻女子唇枪舌剑势不两立的半老男女——自称的表姑和她伟岸的丈夫——猛然冲过去,用力将年轻女子从男子怀抱中扯到自己这边来,那伟岸丈夫又顺势一掌,将年轻男子向后推了个趔趄,随着人群呼啦一声后退,年轻男子被推倒在地下。
“滚!你个小瘪三!你没听她讲吗?这里没你的事儿,有多远滚多远!”
这时有人叫道:
“医生呢?医生不见了!”
医生这会儿已经离开了,他利用了这群人疯狂撕扯的空当,悄悄溜进了空地前方的车场。那里停了更多的车,还有一串串的车开进来寻找已经不多的空车位。已经停下的车上坐著司机,他们中有些人并没有参与到人群的纷乱里去,一个个事不关己地坐在车里玩手机,几个热火朝天打怪的小伙子口中不时发出“嚯”“嚯”的叫喊,以表达着他们的兴奋或者成功,手机屏幕上变幻的七色光反照着他们一张张生动的面孔。医生已经想离开了,他不想继续留在混乱中,但他必须找到那辆接他来的豪华商务车,让司机把他送回去,他自己是不知道路的,但他并没有很快找到。
这会儿他已被另一些人认出来了。这是些一直站在车场边缘、像是并不关心宅门前空地上人群中的争吵、其实却在密切观察事态发展的人。他们中有年轻人也有中年人,但都是男人。医生觉得与方才他走出豪宅大门后遭遇到的人们相比,这些人才是与今晚的事件关系重大的人,或者是他们的代表。
“医生你好,”一个将近中年的男子友好地向他走来,截住了他的路,人很清秀,戴着一副新近流行的白边眼镜,“你是需要帮助吗?……啊,今晚对你来说也是不好过的不眠之夜……”
医生像是被他的话惊醒了一样站住了,下意识地冲他点一下头,就像陌生人相见时要打个招呼一样。全方位的服务。他又想到那个词组了。好像就连这个人也明白他今晚不可能想离开就离开这里一样。不过他心里反感这句话,像方才面对宅门外那黑压压的人群时一样,医生此时也不想回答眼镜男的任何问题,他对这个突然出现的男人既不信任,又觉得不对任何人讲话是他的权利。男人方才的话只是出于搭讪的需要,并不是真的关心他,有点想掩饰什么,有点言不由衷,说不定有别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