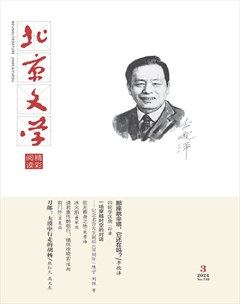一
在铁城,夏天的时候,每逢初三和初八,河对面村子里的人会扯着一艘笨重的木船,从河对岸滑向河这边赶集市。冬天的时候更是方便,就从封冻了的洮河上走。人们赶着驴车,拉着骡子,马背上搭着褡裢,或者背着背篓,也有推了加重自行车的人,老老少少、热热闹闹、喜气洋洋地来对岸采购。
嘈杂的人群里,一方小小的桌子,顺桌子的桌角边放着一台破旧的录音机、黑白电视机,矮小的冰箱。桌子上凌乱地摆满了元器件,桌前立着一个褐色的硬纸板,上面用黑粗的毛笔醒目地写着“修家电”几个大字。
人群中,庆云叔叔埋头正在拆卸着一台18英寸的电视机。他仔细地打开了四角的螺丝,掀开了电视机背面黑色的盖子,那些五颜六色的电线像大脑里的血管一样错综复杂。他低着头顺理着那些永远也没有章法的电线,浓密的头发一直垂在额前,在冬日稀薄的阳光下折射出栗色的光泽,那光的阴影正好打在他英挺的鼻梁上。
庆云叔叔总是将摊位支在我家的大门口,从包里拿出那些长短不一的改锥,再将一些大小不一的螺丝钉倒在方形的铁皮盒里。他将自己收拾得很整洁,总穿一件咖色的帆布夹克,青色的裤子,平底的毛布底鞋。衣服仿佛与他的气质浑然一体,有河水和风的味道。每当见我顶着一头乱蓬蓬的头发抱着破旧的布娃娃从大门出来,他总会会心地笑一笑,笑起来方正的嘴角上扬,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风中,他的眼睛深不见底。
庆云叔叔总会在忙碌的摊位前给我比画一个吃饭的样子。
我摇摇头。他从旁边买包子的店里给我买来两个羊肉包子。
我哈着气站在他的摊位前,边吃包子边看着他安静地捣鼓着桌面上凌乱的电线。有时,他用电笔探一探其中一个绿莹莹的电板就会突然起火,发出一股刺鼻的味道。我在惊慌中后退两步,他见状微笑着摸摸我的头。
庆云叔叔算起来是父亲远房的一个表亲,他家住在村子的东头,大门顶白色的玛尼旗被大风吹得哗啦啦直响。总能看见一个精瘦的老人站在门口,手里捋着麻丝,熟练地转动手里的捻线杆。风里他看上去很是精神,两只深陷的眼睛深邃明亮。他是庆云叔叔的父亲,我唤他姑爷爷。而姑奶奶——庆云叔叔的母亲,是个皮肤白净微胖的妇人,特别爱干净整洁,虽然年岁已去,但她一头乌黑的发在灰色的头巾下还是那样顺滑。用奶奶的话说,她家的地面能照出人影来。
姑爷爷、姑奶奶一共有两个儿子:庆雨、庆云。他们家是一进三院的模式。刚进去是一个顺溜的草屋,和庆雨叔叔用来码放洮砚石原料和制作洮砚的敞篷。第二道门进去是一个紧凑的一套土坯木梁的房屋。院子里干净整洁地铺着洮河边捡来的鹅卵石。细心的姑爷爷还将那些石头按颜色排出菊花样的图案。廊下的台阶也是用那些鹅卵石精心地垒砌起来的。整个房屋被油漆成淡淡的鹅黄色,庆雨、庆云叔叔用他们手艺挣的钱镶嵌了明亮的玻璃窗,看起来特别的透亮。庆雨叔叔的妻子是个爱笑的小眼睛女人,眉宇间稍稍带有一点媚气。在风中,她总喜欢坐在院子的廊檐下织一件酒红色的毛衣。我一直见她织,可总觉得没有织完的时候。
“哎呀,丫丫来看你姑阿婆了。”我进去的时候,她愉悦地笑着,手里不停地织着那件酒红色的毛衣。她笑起来,嘴角有细细的褶皱。她的眼睛远远地向我瞟过来,用余光顺带仔仔细细从头到脚把我打量了一遍。我最不喜这样被人莫名其妙地打量上一番,我最怕那样随意又刻意的眼光,仿佛永远藏着天大的预谋。
穿过一道黑色的狭窄的夹道,就来到了后院。那是一座占地两亩左右的大果园,总飘散一股淡淡的柏木香,这味道会让我想到河对岸原始森林里特有的清香,也会想到正月十五飘散在山顶拜祭山神时煨起的桑烟。风吹一吹那些柏木燃烧后的味道飘得满谷满洼都是。这种味道闻起来古老中略带一丝隐秘。那里错落有序地种着梨树、杏树、苹果树还有零星的几棵桑树,树的枝丫在风中不停地摆动着,发出吱吱的声响。有一条鹅卵石铺就的小径,一直通向靠山脚的五间土木屋。
自庆雨叔叔结婚后,姑奶奶姑爷爷和庆云叔叔就搬到了果园里生活。
姑奶奶做得一手发得掉渣的发糕。我进去的时候,她正从蒸笼里将白净的发糕小心翼翼地搬出来放在桦木的案板上,然后在切得方正的发糕上淋上调制好的蜂蜜。她见到我总一副笑眯眯的样子,笑起来的时候整个人也像一个白净的发糕,甜甜的。她让我先去找庆云叔叔玩,等发糕凉好了她会喊我。
姑爷爷坐在用山羊毛擀成的黑色毛毡上,在擦得锃亮的火盆边上悠闲地喝着罐罐茶。他喝茶的时候总是将屋子里的花窗支起来。风一吹,那些茶香都被带上了天空。他用黝黑粗糙的手指捏捏我冰凉的鼻子,像是叹息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丫丫是个好姑娘,就是总也不爱说话。也难怪你总喜欢来找你庆云叔叔。”姑爷爷说完抽上一口旱烟,眼睛亮闪闪地望着头顶熏得微黑的木梁。
“不要拿丫丫和庆云比,丫丫不是哑巴。”炕沿下姑奶奶边蘸发糕,边向炕上的姑爷爷责备道。
“哑巴也有哑巴的好,至少不会祸从口出。说得少就想得多,你看我家庆云,除了不会说话,那脑瓜子、那长相不比村里其他孩子差。”姑爺爷说完这句话,好像找到了些许的宽慰,继而抿上一口罐罐茶。
我轻轻走进庆云叔叔的房间,他正埋头认真地维修着上个集市上别人给的一个短路的录音机。他修好后,将手掌轻轻挨在喇叭上感受它的振动。
阳光很好,庆云叔叔也支起了花窗。
见我来,庆云叔叔放下手中的活,打开长桌边上的一个抽屉。他从抽屉里变魔术式地给我找出打磨得光滑的石子,还有从南水泉里捡来的黑乌石。我开心地接过那些礼物,对着他张着嘴做出谢谢的嘴形。他微笑着朝我摆摆手。他笑起来的时候,满脸的纯真。我觉得如果有上辈子,我想我或许也是一个哑巴。要不我就是大河边上的一棵树,孤独安静地存活在世上。在风里,在寂静的岁月里,河对岸另一棵树也在艳蓝的天空下,静静地伫立在风中。
路过我家大门口的孩子朝台阶上望望我会嘲讽地喊我一声:“小哑巴。”如果被庆云叔叔看见,他会用手轰走那些取笑我的孩子。
“两个哑巴,爱吃西瓜。吃不到西瓜,哑巴啊啊啊。”那些孩子边走边大声嬉笑着跑远了。
庆云叔叔走过来,坐到我身旁,摸摸我的头,让我摊开手掌。他从兜里掏出从河边捡的光滑的石子,一颗一颗放到我的掌心上。他吹一吹台阶上的土,示意我和他一起玩丢石子。
暮色下沉,天渐渐地暗了下来。
石阶一下子变得冰凉起来,穿过村庄的风也变得紧了起来。庆云叔叔捡起那些石子装进兜里,在暮色里拉着我的手逆风向他家走去。
温暖的炕上,姑奶奶做了擀长面,我一口气吃了一大碗。庆云叔叔喜欢将他碗里的肉夹给我,看着我将一大碗长面连汤带面一起吸溜进肚子,暗黄的脸蛋上渗出一层淡淡的红晕时,他开心地笑了。
“老汉,你说我家庆云要是没被高烧烧成哑巴,再过一两年就要娶媳妇了。”姑奶奶朝坐在炕角阴暗处的姑爷爷说。
火盆里的炭火烧得通红,屁股下羊毛毡的热量噌噌地往上蹿。风吹着纸糊的花窗“嗞嗞”地响。吃完饭,我就着火盆里温暖的火光蜷成婴儿状,顺着炕桌的边沿睡着了。
“丫丫,醒醒,快到家了。”夜风里传来奶奶急促的喊叫声。
四下静悄悄的,只听得见汪汪的几声犬吠和风吹洮河哗哗流淌的声音。月色里奶奶的脸看上去是那样的暗黄,她呼唤我的声音又低又哑,像后山坡旷野里受伤的鸦叫。人老了总是变得性别及面容模糊。奶奶的声音和面容有时候真的很像一个年老的男人。我心里想着将脸埋进了庆云叔叔的背上。
我在庆云叔叔的背上眯着眼睛,我觉得故乡的山川河流都在风中慢慢地后移。我心想,这时候的世界真好,没有一点嘈杂的声音,也没有那么多面目不一的人群。
二
过完腊八的第二个清晨,稀薄的阳光里飘着零零散散的几片雪花,我十二岁了。
还没有吃早饭,家里就突然来了一拨人。他们告诉奶奶,昨天夜里姑爷爷去世了,要借我们家的饭桌和长凳用。
那个早上,空气一下子变得静默起来。风好像也停止了吹动。
我和奶奶随便吃了一点早餐向庆云叔叔家奔去。
还未进门,就见庆云叔叔家的大门上早已经撕掉了过年时贴的对联和门神。走到第二个院落里,堂门大开着。院子西边的一角放着一口没有上色的棺材。棺材脚下摆放着五颜六色的颜料小碟。我们进去的时候,给棺材上色的匠人刚到,正调好了颜料给棺木上色,一笔极致的青蓝描在柏木棺材上,死亡的气息扑面而来。
“舅奶奶和丫丫来了呀,快进屋,你姑阿婆在里面。”干冷的风里,小眼睛女人见我们进来显得很热络。
我朝堂屋望了望,堂屋中间的供桌已经被搬走了,白色麻布帐幔竖挂着遮住了姑爷爷已经冰冷的身体。黄色的干草在帐幔底下的边角若隐若现。风一吹,零散的雪花卷进了堂屋。庆云叔叔从堂屋里走了出来,他头发有些许微乱,单眼皮肿肿的,眼皮上有瘀血快要渗出来。
他走过来,照例摸摸我的头。
我拉了一下庆云叔叔的衣袖,一种心酸至极的悲伤袭上心来。我将下巴缩进脖子上的牛绒围巾里,西北风里大滴大滴的泪砸在我的脚面上。
庆云叔叔仰起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冬日的风里,果园里的树枝投影凌乱。从河边吹来的风,将那飘散的雪花斜斜地吹在脸上,哭过的脸颊刀割似的疼。
庆云叔叔走在前面,我看不到他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