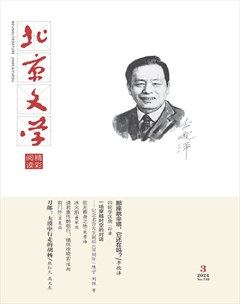一
“五一”长假。
杭城太过拥挤,决定暂不回乡。
浏览家族群聊。“小女人”是谁?问了四哥。答曰:凤霞。
拨通凤霞电话。一声“小伯伯”,亲切自然。还是小时候的味道。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是乡音,是亲情,还是她多难的命运?
询及近况。不在老家杭州,在富阳。大拇指坏了,无法继续餐厅打工,正待手术。
“住在哪里啊?”
“以前打工时的宿舍,和老同事挤一挤。”
“生活好吗?”沉默,几声勉强的干笑。
“不想过去的事了,一想就头痛剧烈。反正错了就是错了,多想也没用”。
“人生短短几十年,不必纠结太多,什么叫对,什么叫错?活在当下最重要。身体有无其他毛病?”
“前些年在广东做过一个大手术,子宫癌,全部切除了。六年多了,现在一切正常,估计都好了吧。”
“平时没有同老家联系?”
“隔几天同老妈视频一次,聊聊天。她也八十多了,住在弟弟家。”
“你多少岁了?”
“比你小一轮,都属蛇嘛。虚岁都奔六十了。”
“时间过得真快。你先把大拇指手术做了。下一步再想办法。振作精神,要加油啊!”
“我没事的,小伯伯放心好了。”
二
凤霞是我大哥的长女。生于1965年。我家兄弟五个,没有姐妹。二哥结婚早,领先生了两个儿子。凤霞的到来,使家里有了第一个女孩儿,增添了生机,全家为之高兴。奶奶亲自赐名凤霞。
凤霞也很争气,从小就长得水灵,是属于人见人爱的那种江南女孩儿。更为难得的是她天生一副好嗓子。十三四岁就进了公社越剧团。唯一不足是个头稍小,只能出演丫鬟之类,总是当不上主角。但她的唱功确实厉害。记得当年我回去休假,还专门为她录了一段“黛玉葬花”,带回北京与朋友分享。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波商业大潮给地处杭州城乡接合部的家乡带来巨大冲击。各色个体户应运而生,地摊经济大行其道,卡拉OK和交谊舞遂成时髦。大量外地人涌入,带来诸多文化碰撞。人心思变,人心思动。社会光怪陆离的快速变化,对年轻人充满诱惑。走对了路,顺风顺水;走错一步,万劫不复。
凤霞属于后者。读书不多,长相出众,性格开朗,头脑单纯。与同乡的几个女孩子一起玩,小小年纪,胆子挺大。她们结识了几个来自福建的小伙子,被对方忽悠得五迷三道。不与家长打招呼,便被带往外地。一去几年,杳无音信。其间,同村的一个女孩曾回来过一次,问她凤霞在哪里,她也说不清楚。因为她们一到那边便被人分头带走了。大致方向是在福建南安一带。于是,大嫂天天以泪洗面,大哥常生闷气,母亲更是焦急万分。好不容易盼到我从北京回去休假,便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到我身上,要求我务必设法找人。
我于1976年进入外交部工作,住在部内集体宿舍。这里除了新干部外,还有一批家在外地的老同志。他们因夫人没有城市户口而被排除在分房名单之外。老陈是其中之一,大我十几岁。他老家福建,太太在农村带着三个孩子,且身患肝炎。老陈生活压力大,平时省吃俭用,过年回老家还是我帮他剪的头发,明明弄破了头皮还说不痛不痛。老陈为人好,业务强,是当时部里为数不多的几个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之一。我们在同一层楼居住一年有余,我经常向他请教各种问题。后来我出国常驻了。老陈则申请回到福建地方工作,担任晋江地区专员一职。
有关寻找凤霞之事,我曾致信浙江省领导和北京及地方的妇联组织,只有浙江省妇联表达了同情,但终无下文。情急之下我给老陈写信求助,内附所能收集到的一切信息。差不多一年之后,老陈来函表示人已找到,让我尽快南下,就地解决问题。
接信次日我便启程。先到老家商量方案,请当过兵的四哥同行。记得当时正值雨季。从杭州到厦门乘火车花了十几个小时。一路翻山越岭,尽管窗外风景奇好,但根本无心欣赏,内心一直忐忑不安,因为根本不知道孩子身在何方,要人過程中又会出现什么状况?设想了无数种可能性。心里仍觉得不太踏实。
从厦门到老陈所在城市泉州还有一百多公里。长途汽车一路颠簸,赶在天黑前抵达晋江地区行政公署大院。老陈家就住在院内职工宿舍。我们在去他家路上遇见一妇人正在扫地。老陈介绍此人正是他太太,是院里的临时工,扫一天地挣一天钱。老陈家三个孩子已转到城里上学。住房面积尚可,已为我们腾出一个房间。晚餐过后,老陈一方面招呼我们,一方面接待了好几拨上访人员。有的要求平反冤假错案,有的要求解决职称问题。看上去,地方工作也不轻松,面对的都是老百姓的实际问题。
老陈向我们简要通报了一下其所了解到的情况。好消息是人已找到,生活在南安县山区某个村子里。坏消息是已经生了孩子。由于当地情况十分复杂,迄未告知当事人我们要来接人的消息。
次日一早,南安县公安局就派了一辆吉普车来接我和四哥。随车还有一位警官。见他腰上别了一把手枪,我瞬间感觉到事情并不简单,此去结果殊难预料。
从泉州到南安县城大约四五十公里。一路泥泞曲折,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从外观看,县城建筑颇具古风,树木青葱,行人稀少,在斜风细雨中有些沧桑之感。
过了县城,汽车接着往山里又行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这里是一个乡公所,是某某乡人民政府办公所在地。主楼建筑依山傍水,窗外就能看到一条不大不小的河。
妇联主任是位干练的中年女士,谈吐热情,且用当地新茶招待。我们边喝边聊,旁边还坐着一位人武部负责人。据主任介绍,该乡地处偏远山区,经济困难,当地年轻男子娶妻较难。这些年,通过各种途径来此的外地女青年、特别是四川女孩儿不少,各地前来寻人的案子时有发生。除晋江公署和南安县方面外,浙江省妇联曾来函询问凤霞下落。乡妇联十分重视此案。知道家属要来,已派摩托车去接人。但所在村离乡公所有相当一段山路,还要摆渡过河,需要一点时间,望能理解。我对妇联协助表示感谢,同时要求务必确保凤霞安全。妇联主任一直变换话题,从乌龙茶到春耕再到妇幼工作,等等。我一边应答,一边不停将目光转向屋外观察动静。两个多小时过去了,院外终于传来“来了来了”的声音。
真的是凤霞。同来的还有一位个头在一米八以上的男青年和一个两岁左右的小男孩。见到我和四哥,凤霞竟然叽里咕噜地说了一段当地方言,我们连一句也没听懂。我试着用家乡话跟她沟通,她像是梦游般地吐出了“小伯伯”三个字,然后站到我和四哥一边,眼神中充满无助。我把她叫到一边,问她要不要跟我回家?她不停地点头。我问小孩子怎么办?她说这是他们家的孩子,应该由男方抚养。
于是,我向在场人士表明,凤霞是被诱拐来的,十六岁还未成年就未婚生子,事属非法。她本人强烈要求离开此地,我今天受家长委托必须将人带走。妇联主任还来不及发言,那位人武部负责人就冲着凤霞大喊:“你是自愿来的还是被拐骗来的?必须先说清楚。”凤霞被吓得不敢出声。我明显感到对方是怕承担责任。而对我们来说把人接走才是当务之急。我随即向妇联主任表明,今天来的目的不是来讨论问题的,孩子十六岁被迫怀孕,从未履行过法律婚姻手续,她个人强烈要求随我离开此地,乡里应当支持其正当要求,责令男方立即放人。妇联主任做了男方工作,操的是福建方言,我猜是在稳定其情绪,说服他同意让凤霞跟我走。关键时刻,县公安局警官发话了。他斥责男方胆大妄为,是严重违法行为,今天必须让家人把凤霞接走,以后也不得纠缠。那位大个子男生基本没怎么说话,我看了他几眼,对他并无太多恶感。他手里抱着孩子,也没和凤霞作更多交流,似乎没有什么心理准备,神情淡然地目送我们上车离开。
凤霞上车不久就睡着了。警官先生一路沉默不语。我可能喝茶太多,脑子里一直闪现那个孩子的镜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对还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