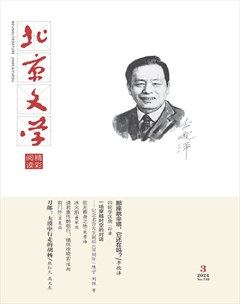伪装成感叹号的人
对有些诗人,一首诗是在写成之前就已写成;对另一些诗人,一首诗是在发生之后才发生。拓野则处于两种状态的叠加态,永远玩味着“已成”和“将未”间的晦明变化。对“不及物”之诗的批评,便也是一种不及物的友谊,是“对于已经发生却没有留下痕迹的事物的友谊,被动性对于未知的非在场的回答。①”
“拯救诗歌史写作的秘诀是,从谨慎的假设出发,大胆地想象李白身上的杜甫”②,或可在拓野诗中想象艾略特身上的钟鸣,想象一种“道术为天下裂”之际将神性羼入历史、对“创世”再演绎的方式。《蝴蝶清啸录》《夜禽盈窠记》运用精心设计的“凑泊的即兴”,前者以诗体复现蝴蝶的头、脸、身、翅、足,以“满园花翎副都统,水草禽兽蝴蝶盔”作为人文与自然的凝聚核,后者则调度“暮归”与“慕归”“若昧”“若类”“若身”之间的幻觉操演,复现生成与幻灭。如拓野所说,他为了处理纯粹势能关系而“把力量都给了平面”。诗的局部器官必须充满字句音律的文字游戏,每一个诗歌细胞内部都要进行分离与媾和,才能再现“无—有—无”的生长过程。
于是,“不及物”的名物罗列和语词杂交便是必然的。拓野曾自陈对注解和译名的洁癖。若如本雅明所说“翻译即转世”,拓野所做的便是榨取拼音字母在象形文字中的转世,给通用译名独家标志:“波莱罗”“维纳斯”,变作“波罗莱兹”“维娜丝”,一如“佛罗伦萨”化身“翡冷翠”。然而,以翻译的手术造作出一种视觉而非内容的诗意,并非对个中的人工成分无知无觉,而是逆练的再逆练(拓野称其为“反用学生气,反用不及物”)。

会员专享,阅读全文请先登录

登录/注册
本文刊登于《北京文学》2024年3期
龙源期刊网正版版权
更多文章来自

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