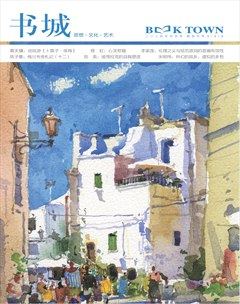选择一种“纯净”的语言
在最初缔造意大利语的几个文化巨擘中,但丁(1265-1321)是敞开的、包罗万象的,代表了某种混杂和无限;彼得拉克(1304-1374)则曲径通幽、向内探索,用一种纯净的语言表露了内心世界的小小颤动。在语言方面,一个很小的例子就可以展示两者的差异。但丁在《地狱》第二十八章中对挑拨离间者的处境进行了栩栩如生的描写:
那人竟被劈成两半:从下巴一直劈到屁眼:
大小肠挂在两腿中间,
心肺肝脾全都暴露在外面
……
(黃文捷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
但丁是写实的,不会用文雅的词汇替换那些略显粗俗的词语;而彼得拉克的诗文中连“腿”这个词都可能会回避,顶多写到“美丽的脚”(bei piedi),根本不会出现“屁眼”和“粪便”如此刺眼的词语。若用现在的话来说,彼得拉克是典型的“内敛型”人格。在《歌集》的开头,诗人就呈现出一个孤单的身影在旷野漫步的形象,躲避爱神纠缠的同时,沉迷于一个万分敏感丰盈的内心世界。
彼得拉克建立的语言典范无疑是成功的,在他离世后一百多年,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语言学家本博(Bembo,1470-1547)提出将彼得拉克的语言作为诗歌语言的典范:因为要把俗语提升为一种文学语言,就要杜绝“俗气”的词语。彼得拉克用佛罗伦萨语言写作,但他和但丁一样,是一个被流放者,他从小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法国的阿维尼翁,又在蒙彼利埃学习法律,后来也在意大利北部生活过几年。彼得拉克几乎没有在佛罗伦萨生活过,他用拉丁语工作,在教皇那里谋了一份差事,他的佛罗伦萨语是一种“流散”者的、书面的语言。当代古典文学学者桑塔伽塔(Marco Santagata)认为:
彼得拉克的语言是现代的。他对于用词格调统一的坚持是对的,一方面排除了过于口语的表达,另一方面减少了对过于艰深的专业词汇的运用,这样产生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词语表。彼得拉克会优先选择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词汇,也就是在语义上有多种涵义、内涵丰富的词语。总之,他的做法是对的,就是凸显一种远离日常的语言,并强调其抽象和形式。
除了词语上的严格标准,彼得拉克当然也倾向于思想上的严肃、优雅,他的诗句定然不会出现同时代锡耶纳诗人切科·安焦列里(Cecco Angiolieri,1260-1313)那种直言不讳、亵渎主流价值的诗句:“把美女都给切科,瘸子丑妇归他人……”或者“世上有三样东西最合我意:骰子、女人和酒馆……”本博不推崇在今天看来引人入胜的“多语体”《神曲》,认为只有《歌集》里严格选择用词的语言才是完美的典范。事实是,在《歌集》出现后的两三百年,“彼得拉克主义”在欧洲盛行无阻。
享受世俗声望的爱国者
彼得拉克其实在生前就备受追捧,他一三四○年在罗马被加冕为桂冠诗人,这是他世俗声望的顶峰。一九○六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意大利诗人卡尔杜奇(1835-1907)在他的文章《在彼得拉克墓前》中,讲述了这种空前绝后的盛誉:
不仅仅是那不勒斯国王、法国国王欣赏他,为他的才华感到惊异;皇帝和教皇也在追捧他;同时意大利各地暴戾、粗鲁的僭主也被他驯服。比如残暴的米兰城主威斯康蒂希望他能当自己的儿子的教父……他当然也不乏民间的追随者,有目盲的老先生由儿子搀扶着,在意大利半岛上追随着桂冠诗人的脚步,还有工匠用鲜红色和金色装点房间来招待他……
彼得拉克是一个“现代人”,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欧洲各地旅居,曾经渴望过古罗马的辉煌能重新回归,甚至指望过先于时代的狂想家,“最后一个罗马平民保民官”—科拉·迪·里恩佐能开创一个新局面。他的梦想太过于超前,很快陷入幻灭,意大利在十九世纪才勉强实现了统一,辉煌却谈不上。彼得拉克是一个世界人,但民族身份却是鲜明的,当时意大利各城邦相互作战,同室操戈,请的都是德国雇佣兵。他和同时代的很多文人都意识到了雇佣兵的害处,在《歌集》里第一二八首就收录了一首爱国诗歌,呼吁意大利人停止内斗,当心德国人的阴谋。
我的意大利,望见美丽的身体上
惊心的疮痍
虽然言语对致命伤
无济于事
但至少我的哀怆
是台伯河、阿尔诺和波河的期望
现在我所处的意大利
痛苦而沉寂
天主啊,我恳求
怜悯让你降临到人间。
眷顾你喜爱的高贵土地。
慈悲的主,你看
一些细小的仇隙
都会引起血战;
残酷而高傲的战神
让人心冷硬,一意孤行
天父,请感化、打开人们的心结
……
在各城邦残酷斗争,甚至城邦内部也不断分裂的局势下,彼得拉克一句深情的“我的意大利”彰显了他的身份归属,也为几百年后“塑造意大利人”开启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