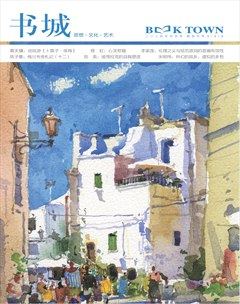从《一句顶一万句》开始,接上《我不是潘金莲》和《一日三秋》,刘震云的三部作品无一例外地都在聚焦人生问题,讨论不同的人究竟会如何对待自己的生活,不同的方式又会带来怎样的结果,甚至,这些不同的态度之间还隐约潜藏着一条逐步向上的阶梯。这一点最直观地体现在各色人物为生活所找到的诸般“出口”之上;在刘震云的叙述里,他有时也称其为人物的“喜好”。
无论是内容,还是创作的野心,《一句顶一万句》都堪称刘震云最成熟的作品;作者曾夫子自道,称自己在此书中约略摸到了中国人生活中最根本的一些东西,它们可以超越历史和政治的变迁。在其中,作者刻画了许多别具一格的人物。最先出场的是赶车的老马,虽以赶车谋生计,却不喜欢赶车。他喜欢“吹笙”。别人赶车打盹儿,他赶车吹笙。最能代表村庄生活之氛围的是杨家庄的罗长礼,本业是做醋卖醋,他的醋却容易变味长毛。他喜欢“喊丧”,掌管丧礼中祭奠次序的调度。还有老胡,延津县的县长。老胡的心思不在白天做官,而在晚上做木匠,县衙的公差都是他的徒弟。别的县衙一股潮气,他的县衙一股刨子花的味道。
这样的“喜好”已经超越单纯的娱乐,而是一种逃离,一个出口,一扇他们为自己打开的窗。或者说是一种生活,一种“生活在别处”的生活。按照小说隐藏的时间线,他们皆是二十世纪初叶的一代人。同样是清末民初,鲁迅先生曾专门讨论铁屋子的问题:如何叫醒沉睡的人们,究竟是拆房子,还是破门而入。以及娜拉出走的问题,离家之后又去往何方。但在刘震云的笔下,这个民族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就算没有出走也早已不在原处,也无须破门而入,因为每个人都为自己打开了一扇别样的窗。
上卷的主人公杨百顺是他们精神的实际代表,不但有“舞社火”这样一扇窗,而且一次次决绝地离开,最后连名字也改成了毫无相干的“吴摩西”。名已无,姓已改,他厌弃的不是自己,而是既有的生活。借着杨百顺的老师老汪解《论语》的话,作者一语道破这些人的心事:“有朋自远方来”为什么让人高兴,恰恰是因为身边的生活里没有说得着的人。老汪是书中唯一的读书人;透过他日常的语调,这些普通人身上似乎都生发着一种存在主义的气息。
值得寻味的是,在《我不是潘金莲》这本书的目录里,作者明确地只把李雪莲两百多页的人生当作“序言”,而最后三十来页的老史的故事才是“正文”。若要理解“正文”所指为何,还得回到老史的生活态度。
老史何许人也?曾为一届县长,现在革职还乡,开了一家饭店叫“又一村”,店里的连骨熟肉远近闻名,日日排着长队。老史平日喜好打麻将,不是没日没夜地打,而是四个老友一周打一次;就像店里的连骨熟肉,虽供不应求,却每天只炖两锅,卖完即打烊。
在杨德昌的电影《一一》里,也会有一个类似的问题若隐若现。电影的主人公是一个中年男人,既不满意在公司里的工作,家里也一团糟。而他的妻子敏敏同样身心疲惫,经常上山去庙里做斋戒。电影的结尾是敏敏从山上下来了,哭着说再也不去了,一家人仿佛重新启程要开始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