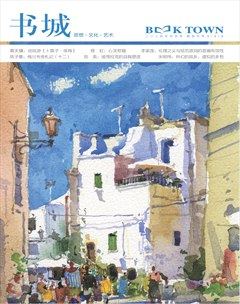一首写给童年的挽歌
小银,从儿时起,我就本能地讨厌寓言。寓言家们借那些可怜的动物之口可没少说蠢话,所以我痛恨它们……长大后,小银,寓言家让·德·拉封丹终于让我和那些会说话的动物和解了,他的话语有时候真的让我仿佛听到了乌鸦、鸽子或山羊的声音。不过,故事结尾的寓意我是不读的,因为那不过是一条枯燥的尾巴,是灰烬,是作者完稿时不慎留下的污渍而已。
——《寓言》
尽管《小毛驴与我》在儿童读物的序列中早已脍炙人口,但不是所有人都有幸在童年便与毛驴小银相逢,或是能准确忆起孩提时初见小银的自己。百余篇散文诗读罢,遇到《寓言》一篇,恍如在莫格尔的海天间骤然升起一道高墙,读者不得不低头沉思、向回折返——不是面向希梅内斯和小银的反思,而是由纸页折回的、朝向自我的反思。那些为了寻找深掩的意涵而剥开的字句,在审读的目光中暴露板结,质询着读者对于寓意的开掘。不必失落于无从寻回的孩童目光,让我们先轻轻掩上自省的热忱,回到与小银结识之前的时刻。
或许是为了给复返于此的成年人提供阅读建议,又或许要向孩子们声明自己不是童年时厌弃的那种寓言作家,希梅内斯在《小毛驴与我》的序中郑重声明:“我从没写过,也不会去写给孩子们读的书,因为我相信他们完全可以读大人的书。”希梅内斯并不否认孩子与成年人读的书之间存在区别,信任属于童年的感知潜能,反而质询了这一肯定话语背面的假设:如果《小毛驴与我》是专为孩子们而作的,那大人们又是否“可以读”呢?当我们翻开这部充满孩童般目光和笔触的作品,当我们把小银的故事“读给孩子听”时,我们自然代入的身份又是否会在某一刻产生动摇?
把手张开吧,让大西洋的微风再次穿过指间,感受自我被遗忘抽离,就像第一次抚摸小银脖颈上的茸毛那样。

会员专享,阅读全文请先登录

登录/注册
本文刊登于《书城》2024年4期
龙源期刊网正版版权
更多文章来自

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