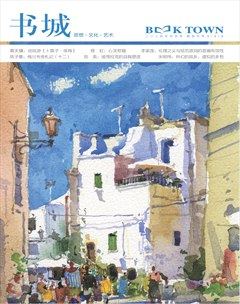一九○三年十月九日,英国作家罗伯特·谢瑞德在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再访儒勒·凡尔纳》的文章,其中记录了凡尔纳这样一段话:
“我的主人公尼莫是一个愤世者,希望跟陆地一刀两断,他从海洋中获得他的动力:电力。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海洋包含电力储备,就像地球一样,不过获取这种力量的方法从未被发现。所以我没有发明任何东西。”
“我没有发明任何东西”,这是时年七十五岁的凡尔纳对自己一生科幻创作的评价,两年后他就去世了。当然,他是自谦,但也传递出一条信息:在凡尔纳看来,他小说中使用的素材,大多来自既有的科学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合理的推演,并非无中生有的“發明”。他的创作,具备强有力的现实依托。在谢瑞德的文章中,还记录了凡尔纳的一段陈述,内容涉及英国科幻作家、《时间机器》作者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我突然想到,他(威尔斯)的故事并非建立在非常科学的基础上。不,他和我的作品之间没有关联。我是利用物理学。而他在发明。我用大炮发射炮弹前往月球,这里面没有发明。他乘坐飞船前往火星,飞船是他用一种消除了万有引力定律的金属建造的。这非常有意思,”凡尔纳先生用一种生动的方式大声说道,“但是请给我看看这种金属,让他去把它造出来。”
尽管凡尔纳比威尔斯年长近四十岁,但后人将他们一同视为科幻小说这一文学类型的奠基人。凡尔纳本人对威尔斯的著作相当熟稔,而且对其飞扬的想象力颇为赞赏。不过在凡尔纳的这段论述中,他着重强调了自己与威尔斯的差异,也让我们对他本人的写作方式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他不会使用现实中不存在的金属,不会去“发明”物理学原理,他只是对现有的素材进行重组和放大,如发射巨型炮弹把乘员送往月球,让读者产生惊奇之余,依然觉得一切合情合理。
以《海底两万里》的核心载具“鹦鹉螺号”为例,早在一八○○年,也就是《海底两万里》出版七十年之前,爱尔兰裔美国发明家罗伯特·富尔顿就研制过一艘人力潜水艇,并将其命名为“鹦鹉螺一型”,在法国塞纳河上公开展示。事实上,凡尔纳笔下的鹦鹉螺号,正是对富尔顿原型潜艇的充分系统化、完善化,在保留了诸如指挥塔、储气舱、储水舱、螺旋桨、升降舵的基础上,增加了船体的吨位、装甲、电力系统以及一系列生活舱室与机械装置,而这些增项在现实生活中同样存在或多或少的实际应用。据说,凡尔纳在创作《海底两万里》期间,还专门参观过法国海军的新型潜艇。所以,他的写法不是无中生有的臆造,而是以现实为依据的推导,具有极高的可接受性。在一九○四年的一次访谈中,凡尔纳明确指出:
以鹦鹉螺号为例,如果认真想一想的话,这就是一种无甚特别之处的水下机械,也没有超出当前科学知识的边界。它通过完全可行而且众所周知的过程上浮或下潜,其制导和推进方面的各种细节全都完全合情合理而且可以理解。它的动力甚至都不是秘密:我求助于想象力的唯一一点是这种力量到底如何应用,在这方面我故意进行了留白,让读者形成属于他自己的结论,这只是一个技术方面的空隙,完全可以由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头脑加以填补。
与后世那些银河帝国、赛博朋克或者末日废土式的科幻小说不同,后者即便对现实进行了某种隐喻或指涉,其世界观构架也会让读者在阅读经验中保持一些基本的距离感:“这不是现实世界。”《海底两万里》从第一章开始,为读者带来的就是一种近乎“现实”的带入感。用凡尔纳自己的话说:“我总是试着让自己哪怕最狂野的小说也尽可能写实和真实。”
作为一本出版于一八六九年的小说,作者将时间背景设置在一八六七年前后,这对当时的读者而言正是当下,天然具备一种代入感。书中不厌其烦地反复提及十九世纪中叶真实存在的各类信息,从那些知名或不知名的生物学家、海洋学家、航海家、探险家,到当时科学界时兴的种种生物分类法与海洋学理论,再到某些众所周知的神话传说和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其目的正是为了让读者沉浸于一种现实与精神的世界。书中甚至会时不时出现一些近乎纪实的叙述风格,让读者感觉似乎在阅读一份真实的“见证”。
纵览整部《海底两万里》,既不是单纯以情节取胜的猎奇之作,也不是专为青少年撰写的童书故事,它是真正带有探索精神的文学经典。凡尔纳将科学、神话与历史融为一体的大叙事,在一个半世纪之后依然焕发经典的启示,那就是知识与想象,以及现实关怀。
科 学
在整部《海底两万里》中,科学方面的内容可谓不胜枚举,这一点从小说人物的身份设置上便一目了然:尼莫船长,国籍不明的神秘人物,精通多门外语的天才工程师,孜孜探索海洋奥秘的大学问家,坚持抵抗殖民压迫的反抗斗士;皮埃尔·阿罗纳克斯先生,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教授,法国生物学家亨利·米尔内-爱德华的学生,两卷本学术著作《海底之秘》的撰写者;生物分类学的狂热爱好者、忠仆孔塞伊,以及一心逃跑的暴脾气鱼叉手尼德·兰德。在这四位主要人物中,尼莫与阿罗纳克斯本就具备博物学家的身份,而孔塞伊的分类学爱好也成了凡尔纳描述各类海洋生物样本的重要载体。在第一部第十一章“鹦鹉螺号”中,凡尔纳详细列举了尼莫船长书房里的藏书,内容涉及机械学、弹道学、水文学、气象学、地理学、地质学、博物学,等等,这些内容在《海底两万里》中全都有所涉及,在鹦鹉螺号环游世界的过程中,凡尔纳见缝插针地把这些科学信息融入故事之中:鹦鹉螺号的动力舱室、亚伯拉罕·林肯号的火炮射击、黑潮与湾流的运行路线、马尾藻海的形成因由、海中火山岛的岩石成分等。可以这么说,尼莫船长在鹦鹉螺号上的藏书,几乎等同于凡尔纳创作《海底两万里》的参考资料。
小说中出现了很多在当时颇为新锐的科学理论,其中占比最大、分量最重、给人印象最深的无疑是对于各种海洋生物的细节描述。这些主人公们一路观察到的生物样本既是这场海底之旅的必然组成部分,更呈现出一个神秘幽远的水下世界。这种文学效果不仅来源于凡尔纳对于各种光怪陆离的生物进行的翔实刻画,甚至他对于各种鱼类、鸟类、植形动物、节肢动物、软体动物的命名方式本身,就已经给读者带来了一种巨大的陌生感。钱培鑫在译林出版社旧版《海底两万里》译者序中便曾指出:“作者的语汇丰富,许多术语深奥冷僻,普通读者难以全部理解,而这种隔阂反而营造出一种诗意,奇异的音韵结合又产生美感。”
在原文中,凡尔纳使用了很多转译自拉丁文的生物名称,这虽然是当时欧洲生物学界通行的做法(至今依然如此),但对于读者来说,除了海洋生物学专家,即便一位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法国成年人,也难以直接领会这些拉丁化词汇的实际意义,这就类似于中国读者遇到“鳓、鲰、鲐、鳋、鲐”之类的生僻字一样,至多只能大致猜测“这可能是某种鱼类”,然后带着一种模糊的不确定性继续阅读下去,并由此产生一种陌生化的阅读效果,引发读者对于未知事物的惊奇。这一点,无论对于十九世纪的法国读者还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读者来说,其实别无二致。与此同时,凡尔纳在小说中的命名和分类,绝非他的凭空臆造,而是充分借鉴了林奈、居维叶、拉塞佩德等诸多生物学家的看法,放在十九世纪中叶的语境下,堪称严格、精确的科学论述。当然,不可否认,时过境迁,其中许多命名方式放在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已经得到了更新或修改,有些分类方法甚至被现代生物学完全推翻、另起炉灶了,这是人类观测手段强化与认知领域扩展之后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