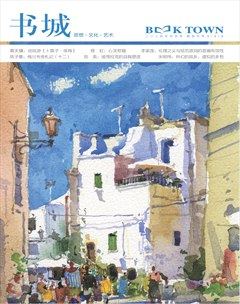一六八八年,一心复辟罗马天主教的英王詹姆斯二世仓皇出逃法国,他的女婿兼外甥、荷兰第一执政威廉三世入承大统—没有经过流血牺牲而实现政权更迭,是所谓“光荣革命”。革命后,两位“共主”威廉和玛丽颁布一系列新政,赢得维新派满堂喝彩,但同时也遭到保守派强烈反对—其中反应最为激烈的是当世大诗人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由于心系故主,德莱顿不肯归顺新君,被褫夺“桂冠诗人”的头衔(改由其文坛劲敌沙德维尔[Thomas Shadwell]继任),与之一同失去的,是王室赐予的不菲年金。年近花甲的诗人迫于生计,转投文学翻译市场,期待有生之年能够完成皇皇三巨册的古罗马诗人维吉尔《作品集》(包括《农事诗》《牧歌集》和《埃涅阿斯纪》)的翻译。
照德莱顿远房表亲乔纳森·斯威夫特的看法,这位复辟时代代表人物最大的特点是“善变”。德莱顿出生于清教家庭,对“护国公”克伦威尔开创“英格兰共和国”(Commonwealth of England)的伟业仰慕不已。一六五八年,在克伦威尔葬礼上,德莱顿与曾任共和国外事秘书的弥尔顿(以及曾担任秘书助理的诗人安德鲁·马维尔)一同追缅先烈。不久,德莱顿发表长诗《英雄诗章》(Heroic Stanzas,1659),表达对克伦威尔的绵绵哀思,在文坛一鸣惊人。又一年(1660),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德莱顿迅速抛出长诗《星辰归来》(Astraea Redux),歌颂查理二世拨乱反正,乃天命之所归—他长期流亡海外令英格兰国家和人民惨遭蹂躏,愈演愈烈的宗教纷争几乎要将英国彻底“撕裂”。德莱顿认为,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表明上天垂听了人民的呼声,正如日记作家约翰·伊夫林在查理二世入城仪式当天记录的那样:“我从未像今天这般开心过,我站在斯特兰德(Strand)大道,观看这一切,并感谢上帝。”
一六六七年,伦敦大火后,德莱顿又发表现代史诗《奇迹之年》,讴歌国王(及王弟)在大灾面前临危不惧,以身垂范,率领国人致力于灾后重建,使得伦敦“如凤凰涅槃般”重获新生。国王封赐德莱顿为“桂冠诗人”,从此之后,为王室撰写王子诞育、公主大婚之类“应景诗”也成为他义不容辞的工作职责。然而,这位诗人似乎走得更远,以致有深度“干政”之嫌。一六八二年,德萊顿创作政治讽喻诗《俗人的宗教》,竭力维护英国国教的正统地位,同时猛烈抨击那些不从国教者、天主教徒及无神论者。一六八五年,风流成性的“快活王”(Merry Monarch)查理二世去世,无嗣,王位由胞弟詹姆斯二世继承。两年后,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发表《信仰自由宣言》(Declaration of Indulgence),名义上要求天主教与非天主教者“同样享有信仰自由”,事实上要求英国人“改宗”。响应国王号召,德莱顿发表《牡鹿与豹》,用“奶白的”(milk-white)牡鹿形容罗马天主教纯洁无瑕,而将英国国教比作凶残的花斑豹。与此同时,德莱顿本人以身作则,旗帜鲜明地改宗罗马天主教,甚得国王欢心。
数年之间,德莱顿政治及宗教立场前后反差如此之大,颇令人震谔。照约翰逊博士的看法,德莱顿一向善于审时度势,其为人和为文一样,“遵循‘适当’(propriety)原则—即艺术审美与现实生活均按‘比例’(proportion)行事,让局部服从于整体,方法服从于目的”。换言之,即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尽管同为新古典派的约翰逊博士竭力为德莱顿辩护(“如果说德莱顿变节,那么,他是顺应英国民情而变节”),但时人似乎对此并不买账。
德莱顿选择维吉尔《作品集》固然出于他对古罗马经典文学的倾慕和向往,但同时也有仿效前者做“帝师”的欲望:维吉尔曾循循开导罗马帝国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注重文化建设;德莱顿也想讽喻威廉国王“偃武兴文”—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奉行“荷兰至上”原则,热衷于欧陆战事(誓与路易十四抗衡),结果导致英国国民税赋剧增,民怨沸腾。王公贵族中不乏拒绝向新君效忠之人,德莱顿后来在维吉尔《作品集》中将埃涅阿斯称为“一位被选举的(elective)国王”,并表彰他在岳父在世期间,从未“要求王位继承权”—所指为何,也就不言而喻。《埃涅阿斯纪》竣工后,德莱顿拒绝了出版商将此书敬献威廉国王的建议,一部分原因是当时威廉的岳父詹姆斯二世尚在(处于其表弟路易十四“保护”之下),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他认为威廉的王位乃是由议会“授予”—威廉首先需要签署《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保障英国人“自古就有的权利和自由”—国王作为“虚君”,其身份大抵相当于职业经理人。这也是德莱顿胆敢在书中影射新君的根本原因。
德莱顿敢于跟国王叫板,当然更源于自身的底气。他不仅是当世最著名的诗人,也是最著名的剧作家、批评家(约翰逊博士在《诗人传》中公允地推许他为“英国文学批评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