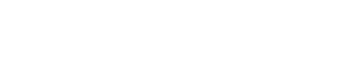镜头对准佘诗曼。
48岁的她,扛住岁月的侵蚀,阔别6年后,回巢加盟台庆剧。
《新闻女王》热度炒起,她顺势加冕女王,三封视后,食尽大女主红利,让港剧市场在风雨飘摇之际,暂觅一处避风港。
独立女性,职场斗争,封心锁爱,终成女王。大女主式的爽剧叙事,成为当下影视市场快消品,却也变得同质且廉价。
资本的侵入,工业化的生产,相同的公式,相似的脸谱,让女性“成长”的影视化创作,只有“成功”,而看不到“长大”。“大女主”华丽长袍下,是慕强和贪权的本质,是社达主义与丛林法则的内化,而不见人的价值与权力的反思。
从前佘诗曼演过的大女主,绝不是那么单调而重复的。
看着她的脸,众多角色脸谱逐帧在脑海放映,突然,放映机停下转动般,记忆停留在一套清宫造型上。旗头、步摇、斗篷,董佳·尔淳,黛眉轻蹙,背后红墙青瓦,白雪薄盖。尽管冬日暖阳倾泻,却令人倍感冷清阴森。
庭院深深深几许,金枝玉叶,情洒宫闱处。可叹帝王留不住,徒留雪地飞鸿去。
20年过去了,《金枝欲孽》在终局留下的悬念,仍在牵扯几代观众的心。
在天理教叛乱中,尔淳逃出宫外后,有安身于安茜那个开满小黄花的故乡吗?与她一同出逃的安茜,在身受暗箭之后有无得救?全剧唯一幸存的男性角色孔武,是否后悔为了功名利禄闯入皇家禁地?留守宫墙之上的如妃,是否怀念在死后还被用来争宠的亲生骨肉?葬身火海、相拥而死的玉莹与孙白杨,一生权斗只换来最后一刻的情动,是否值得?
情欲与权力交织成笼,围困金丝雀,笼中互斗,难有清醒之人,如何能冲破这千年的牢笼,逃出生天?
导演戚其义自己也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最关乎人性”,“人性很有争议性,也会给大家带来共鸣”。
而《金枝欲孽》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是宫斗剧的开山之作,还在于能看见人、人的价值和人性。
这才是一部经典剧作的内核,而非《新闻女王》的“爽”感可以比肩。
颠 覆
2003年,凭借“天地三部曲”,戚其义已在TVB确立“金牌监制”的地位。但他已对那套豪门商战的男人戏感到倦怠,他想做一些“自己以前没做过的”。
他继续找到老搭档编审周旭明,一年的时间里,他们手拿着报纸研究,比较时政、家庭、婚姻、女性等话题和新闻,着手研究女性群像戏。很快,《金枝欲孽》头20集的剧本出来了。
有别于过往金庸武侠剧里的江湖儿女的爱恨情仇,或是时装剧里都市职场的男欢女爱,《金枝欲孽》将故事背景放置于紫禁城,借后宫佳丽相互倾轧,以身体劳动(怀上龙胎)和情绪价值(奉命服侍),来博得皇上赏识,妃嫔封号,可比喻现代职场白领的生存法则。
这意味着,《金枝欲孽》其实是披着古装外衣的现代职场剧,是以当代人的视角去剖析后宫场域里的生存斗争,其内核,是现代的,进步的。
一场戏便可体现《金枝欲孽》的现代视角。
婢女素樱被当作替罪羔羊而无辜冤死,庶民孔武为她出头,将她遗留的笛子放诸太庙牌匾之后。如此一来,帝王妃嫔每每拜祭先祖时,就是“主子向奴才叩头”。
当创作者抛弃了对弱者的同频共情,转而将聚光灯对准上位者,他们无法再有理想和能力想象一个众生皆平等、一切皆有可能的世界。
颠覆君臣之道的立意,寥寥几笔,干净利落,让人不得不赞叹戚其义的鬼才。
20年后,尽管《新闻女王》繼承了香港职业剧的专业精神,大幅度展现了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伦理职业道德,但《新闻女王》里的一众小人物,许诗晴们、徐晓薇们,缺乏理想,只有利益,甘心听受上司的摆布和操纵,作为新闻从业者,不探究精进业务,反而互相使绊,服侍上级,斟茶递水,伏低做小。
打工人,只剩打工,而无人格。
哪怕她们想过也试过反对、反抗、反击。
但对不起,当下编剧们的视角决定了,文慧心才是主角,一个坐稳在女王宝座的上位者,缺乏对下位者的同理心,只有无尽的打压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