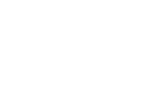猫猫鱼和东坡肉

楼上的邻居在屋顶修了一个花园,栽上各色花树,放上太阳伞、桌椅,我常常在天色将明之时上去看朝阳,读书,写点东西。因为是借邻居的地方,故将其命名为“借园”。今天这个故事,就是借园的主人朱女士给我讲的。
朱女士的父亲是一位老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她的生母是一个能用俄语朗诵普希金诗歌的文艺兵。朱女士的父母郎才女貌,儿女成双,幸福得羡煞旁人。20世纪60年代中期,朱女士的父亲被批斗,朱女士的生母决绝地和他划清了界限,斩断了包括儿女在内的所有联系,以保全自己在省歌舞团的工作。
后来,父亲被发配回原籍,唯一的“行李”便是一双儿女,儿子5岁,女儿3岁。老屋早已不在,生产队腾出一间保管室供他们居住。保管室除了一个扣起的拌桶,什么都没有。父亲早年当过篾匠,从后坡拖回几根竹子,剃枝砍丫,不出半日就拼出一张竹床、一张小桌、三只小凳,他把随身带的军被、饭盒、水壶往上一放,勉强算得上一个家了。三块石头支上一个长条饭盒,烧了开水兑灰面,他们那天吃的第一顿饭,是糨糊。
晒坝西边还有一户人家,住着母女俩,与保管室相距三四百米。据说那母女俩是地主,与村里人没什么来往。地主婆60多岁,膝盖有病,走路一瘸一拐,她的女儿三十几岁了,一直没有出嫁。
地主家的小姐,通常是令人浮想联翩的,但这个小姐和想象的不一样。她没有白皙的皮肤,也没有光亮柔顺的头发和纤细柔美的腰肢,更没有不沾阳春水的纤纤玉指。她面色青黄,头发发黄而且开叉,小眼睛,大脸盘,一对龅牙很不安分地露在外面。
就这样,一东一西,两家成了邻居,灯火呼应,炊烟融聚。一来二去,彼此也有了些小小的照应。

会员专享,阅读全文请先登录

登录/注册
本文刊登于《读者》2024年8期
龙源期刊网正版版权
更多文章来自

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