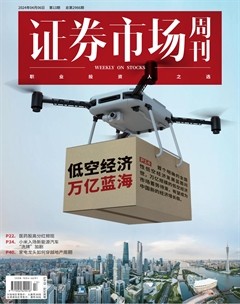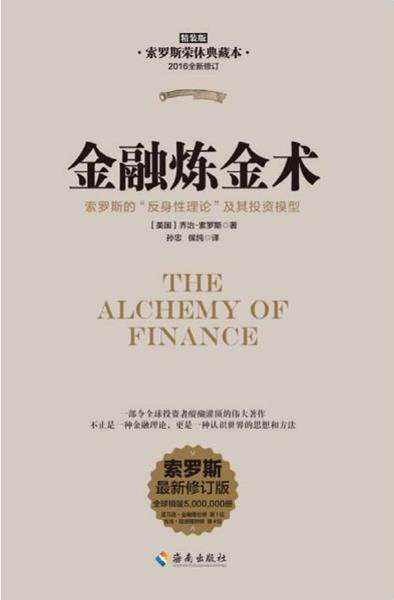
索羅斯原本预期全球性的信贷扩张会在1982年进入反身性的崩溃过程,信贷扩张会随着债务国偿还意愿减弱和银行危机结束,然而他低估了美国作为最后贷款人的意愿和能力。
3.里根大循环
1980年上台的里根政府面临着双重矛盾:一方面是小政府的减税意愿与维持军备竞赛的财政压力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则是供给学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主义的货币政策之间的矛盾。
供给学派的财政政策是全异命题,要么全对,要么全错,这是因为供给学派政策的反身性特征,减税刺激产出,产出增长刺激税收总额增长,这样通货膨胀也会得到抑制,实际税收增加又使预算恢复平衡,这一过程的实现建立在企业家和消费者对减税刺激的信念上。
1979年10月美联储调整了政策手段,从控制短期利率转向控制货币供应量,让联邦基金利率自由浮动,利率的飙升随之而来。利率上升带来的储蓄增长无法平衡减税和国防开支导致的赤字,发债又继续加重政府支出压力。然而最终的结果并不像亨利·考夫曼(Henry Kaufman,80年代最著名的末日博士)在《信贷评论》当中警告的那样,政府提供的高利率挤出国内私营部门的贷款者,而是挤出了其他外国政府,从而引发了国际债务危机。
而美国则是从1982年放开预算赤字开始,一切都突然走上了正反馈的道路,“复苏和衰退一样强劲”,国防开支和政府支出增加,个人实际收入也在增长,公司的财务报表受益于加速折旧和税收抵扣,最重要的是银行变得急于放贷,也开始争夺存款,金融投资者看到了比政府债券更加有利可图的银行利率。
自我强化还出现在美元上,强势美元和高企的利率吸引了进口和投机资本,实际上起到了平抑物价的作用。强劲的经济增长、强势货币、不断增长的赤字和贸易逆差,这就是“里根大循环”。里根大循环与里根的施政理念不谋而合,是里根抓住了闪现的反身性的机会,而且能够坚决抵制使预算重回平衡的诱惑。
里根大循环事实上是从出口初级商品的债务国身上吸血,因为其高实际利率和苛刻的贸易条件,使出口同质化商品的债务国别无选择;欧洲的工业化国家则面临另一种压力,向美国出口固然有吸引力,但是扩大再生产的吸引力远远不如持有美国的金融资产。此时(1982-1985年)的日本是最大的受益国,巨大的出口盈余、强劲的国内储蓄被资本输出抵消,形成了美国的镜像。
另一个反身性过程是预算赤字会从生产性部门掠夺资金,这个过程同样会潜伏在投机资本流入的过程中。
里根大循环的根本是循环和反身性的过程持续刺激货币强势。索罗斯指出了最终破坏大循环的关键因素,是债务成本(原文是“偿债负担”)的持续增长,会导致汇率的下跌。汇率逆转投机资本流向是大循环崩溃的核心原因。
4.银行与公司并购潮
在国际债务危机发展过程当中,银行持续提供增量资金至关重要,但是银行需要在报表上维持未受损失的表象。美联储行使最后贷款人的职责,而欧洲国家的中央银行鼓励商业银行建立储备并冲销坏账,然而更多秘密储备也随之出现。英国介于二者之间。
美联储的纵容导致美国的商业银行作为银团的核心成员,不得不在为真实收到现金时维持账面的高利差,增发贷款以维持资产负债表,要么发展表外业务,要么发展中间业务,当杠杆并购出现时,完美契合了美国商业银行粉饰报表的需求。
银行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股票市场上的折价,导致其无法通过股票市场融资,缺乏股本金导致合并求生。实体企业通过少量资金控制了受监管和存款保险保护的金融机构,利用其贷款业务支撑股东的经营活动。
美洲金融公司(Financial Corporation of America,于1988年破产)在收购第一租赁(First Charter Financial)之后,利用其受存款保险保护(由FSLIC,即联邦储蓄与贷款保险公司承保)的地位,以经纪人和销售团队扩张举债,收购不动产贷款和MBS等业务,在开发贷当中拆东墙补西墙。
FCOA存款规模在两年中扩大400%,财务状况在利率冲击当中恶化之后又得到救助。
在银行危机的反身性过程当中,监管作为参与者的角色起到了关键作用。监管滞后于事件,管理层出手制止过热时,危机已经发生,其作为会加速事件反方向的发展和恶化。抵押品价格的崩溃总是发生在监管作为之后。
管制的最后一招是鼓励并购,鼓励那些最大的银行去收购濒临破产的小银行。索罗斯担心这样的结局是最终拖垮大银行而无人收购,但是他错了,there is always a bigger fish。
企业集团化并购则是另一种反身性过程。技术上讲,企业的集团化并购就是以“浮夸的价格”出售自己的股票,同时以较低的价格收购其他公司的股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