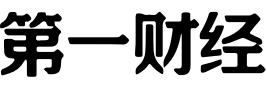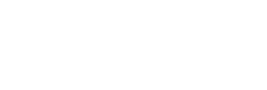Yi:YiMagazine
M:孟庆延
01
Yi:在整个学术生涯以及成长过程中,对你影响最大的社会学家或者思想家是谁?
M: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马克斯·韦伯。大家会觉得韦伯过时了,或者说韦伯那一代人过时了,但我觉得他一点都没有过时,雷蒙·阿隆把韦伯称为“我们同时代的人”。韦伯和他那一代人所提出的一些基本命题对我们来说,依然有效。如果用特别通俗的语言来说,韦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率先在西方产生?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似乎平平无奇,但是他的回答路径不是从传统的政治哲学角度,讲启蒙运动以来个人权利的伸展;不是从政治角度答,讲民主制度的出现;也不是从技术角度,讲爱因斯坦、牛顿以及电力的发明。他就是提醒我们要注意西方文明一个特别重要的转折:宗教改革。在宗教改革之前,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在对抗人性的恶或者否定人性恶的一面。比如在那之前,挣钱是没有正当性的,想挣钱无非证明你贪财,西方小说里就有好多贪财鬼的形象。但宗教改革之后,挣钱的意义变了,它既不是虚荣,也不是贪婪的表现,反而成为一种证明上帝荣耀的象征—要成为上帝的选民,你这辈子要做的就是好好在职业领域工作、挣钱。这会让你觉得工作不是为了挣钱,而是天职,是上帝的召唤。挣钱这件事也就具有了神圣性。实际上,追求利润是人类的本性,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并不只是追求利润,而是通过理性化的劳动组织方式,通过一系列标准化、流程化的生产方式,以效益最大化的方式有组织地追求利润。这就将资本主义精神中最核心的一点—也就是理性化—突显出来。韦伯讨论资本主义精神与宗教改革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在解释宗教改革与现代文明中的理性精神之间的选择性亲和。
韦伯在讨论里讲到的很重要一点就是,当去除宗教神秘主义后,世俗化宗教会特别贴合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就是口腹之欲、趋利避害,以及用小成本换高收益。在这意义之上,我们看到这一百多年来慢慢演进,也就有了工具理性的泛滥。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写的最后一段,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是对现代文明的一种悲哀预言。他说人类会陷入工具理性所编织的劳动中无法逃脱,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寻求成本与收益比例的最大化,事情本身的意义已经不重要了,寻求目标最优解成了意义。但事情的意义本应该超越于此。韦伯对现代世界的预言,包括他提问的方式对于我而言影响很大。我们太活在今天的生活里面,觉得创新特别重要,觉得进步特别重要,觉得发展特别重要,太过追求新的东西。但其实很多所谓新的东西可能只是一些现象,本质可能一百多年来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02
Yi:所以有人也说“向往成功”是工业社会经济发展下的一种叙事神话,萨林斯就讲到原始人每天只劳作三四个小时。从这个角度来讲,“躺平”不是罪恶,更不是问题,更大程度的问题可能是我们被当代生活骗了。
M:是的。第一点,我认为成功学是历史上最大的骗局。因为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真正成功的案例可以被复制,但是成功学一定会讲出可复制的逻辑来。第二点,我认为躺平不是罪恶,当然,这里我们必须将极端的情况剔除出去,这个极端的情况就是一个人吃穿不愁,就甘愿躺着。大部分人其实是没有办法接受自己长时间躺平的生活的,整天睡醒就吃,吃完了就睡。哪怕财富自由的人,也总得给自己找点事做。极端躺平的状态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存在,但不会一直存在,绝对躺平和绝对内卷都有违人性。所以,当我们谈到躺平,“小富即安”式的躺平和彻底躺平绝对不是一件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躺平不是罪恶。
03
Yi:你的研究兴趣很多都在历史之中,为什么?
M:我觉得很多新闻和热点本质上是一回事,无论是热搜、政策还是国际秩序,基础逻辑并没有跳出现代世界来临之后的基本框架,仍然在这个时代的脉络里,还没有进入全新的状态。从人类发展史来看,从中世纪的终结到现代社会的来临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这样的变革时代不会特别多,所以我就看到好多现象,它背后的逻辑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讨论教育平等,其实跟追求颜值正义是一回事,逻辑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