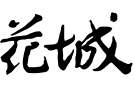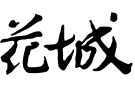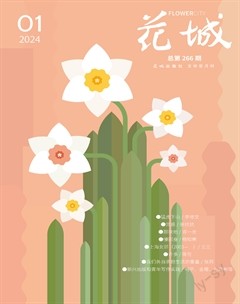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有一年多时间没有回乡了。趁着暑热中短暂的平静,带小孩回家住上一旬。
甫一回来,头一夜凌晨为鸡声唤醒,“咯喔喔——”在深夜模糊而脆弱的困倦中,洪亮而略带悲哀的声音从窗外响起,和着远处别人家的鸡声,一声接着一声,这才发现,原来是爸爸又养了一二十只鸡。其实一回来我就看见它们,只是那时还没有想起鸡叫这件事,这时且意识到有好几只公鸡,鸡笼就摆在我房间正对着的场基上,是以听得这样真切。
我的房间窗外是家里的场基,房门连着堂屋,床头和堂屋只一墙之隔,确切是家里最吵的一个房间。每年回家,我都会痛苦地发现,爸爸又养了一大堆家禽,让我夜里睡不着觉。前年是上百只鸭子,每天天蒙蒙亮就嘎嘎嘎嘎嘎叫着要人放它們出去,直到有人起来把它们放到池塘里去为止;去年是一群大鹅,天亮时叫声嘹亮如一个营的军号,在人的鼓膜里反复振荡;今年则就是这群公鸡了。本来,夜里我就难以入睡,以至到鸡叫时,常常不是还没有睡着,就是刚睡着一会儿,于是只好躺在床上,从三点到五点,听着公鸡们几乎只是稍作停歇,一声接一声地挨个打过自己的三遍鸣。这时天已经蒙蒙亮,爸妈也起床了,把它们放进发白的黎明里,而后是他们说话、做事的声音,直到他们把家里的事大概弄清,到田里去做这一日的农事,鸡们也散开到稍远一些的地方,咯咯咯咯叫着觅食。屋子里又恢复短暂的宁静,我才感到重新涌来的睡意,在小孩没有醒来之前,抓紧时间,模糊睡上一会儿。
因为没有精神,回来的头两天我几乎没有出门,除了早晨起来,骑电瓶车去镇上给家里买一点东西之外,就都闷在房间里。白日里太阳烤得火热,也使人出不得门。出发去镇上时,通常是八九点钟,这在乡下已是很晚的时间,太阳已照得人身上发烫,但怕小孩觉得无聊,无论有事没事,我差不多每天总要到镇上去一趟,买些小孩吃的零食,想象中爸妈需要的东西,拿快递,回来也不过四五十分钟。回来后我打扫卫生,把开了一夜空调的房间门和窗户打开,打开风扇,让空气流动起来。现在,即使是在乡下,我也要把自己房间地板擦得干干净净,桌子整理清楚,为的是有赤脚在房间里走或随时在地上躺下的自由,使有些挣扎的心能恢复少许秩序,不至为那眼目所见的凌乱淹没。不多时小孩便要求重开空调,他比我怕热,有时在房间玩着,大滴大滴汗珠便顺着额头淌下,于是门和窗户重又关上,空调重又打开,但白天的屋子仍使人心情稍加明朗,从窗户透进来的光使得屋子显得通透明亮,仿佛空间也随之扩大了一些似的。屋子里那么凉,对映着玻璃外耀目的光线,使人感觉到仿佛人生中如同一层薄膜般隔着的不真实。
在空调房里待久了,偶尔从房间走出来,去外面收一趟妈妈早上晾好的衣服,那么一小会儿的工夫,也觉到太阳投在薄薄的皮肤上那脆热的焦灼。怕衣服败色,妈妈把它们晾在楼房的阴影里,常常在太阳晒到之前,风就已经把它们吹得焦干了。夜里打鸣折磨我的大公鸡们,白天就施施然躲在门口树荫下睡觉,或是在场基上、空地间踱来踱去,低头觅食,间或打一声悠长的闲鸣。看见它们这么悠闲的样子,我忍不住跟妈妈抱怨,夜里那鸡吵得人睡不着觉!妈妈说:“那鸡笼是离你窗子太近了,晚上叫爸爸一起把鸡笼移一下,移远些,大概会好些。”那天黄昏,妈妈就叫爸爸一起把鸡笼抬起来,往场基角落移了一点,避开我的窗户。从那以后,虽然每天凌晨还是会听到鸡叫,但那已是我自己的缘故,鸡鸣声小了许多。
到黄昏时天渐渐凉下来,如果有风,六点以后会感觉凉爽。小孩被拘了一天,这时常要出去玩,于是我又推出电瓶车,带他到上面或下面村子,沿着村道漫无目的地骑一会儿。村子四面全是稻田,这时节碧绿森森,几乎看不到人影。白鹭从稻田和远处大坝子的竹林上空飞过,山斑鸠在路边停着,见人靠近,便惊飞拍翅,落到稻田上空的电线上,发出温柔的“咕——咕——”的吞鸣。夹杂在山斑鸠随处可闻的咕咕声中,时不时传来强脚树莺极为清脆流丽的一啼,却总是看不见它们的身影。燕子也总在飞着,家燕和金腰燕,许多是今年的新燕子,学飞后还不久,在清晨和傍晚的村子和田畈上空,或是人家的屋顶,无论何处,都能看见它们独自或成群盘旋的身影,或是在屋后电线上,几只一起停着,以喙理羽。黑卷尾常常停在路边电线上,浑身漆黑,两边长长的尾羽撇开成一个温柔的长长的“八”字。远远分岔的小路上,几只不知什么鸟在地面蹦蹦跳跳觅食,一只棕头鸦雀从路边翠绿的野竹枝间翻坠出来,可爱的圆脑袋滚了一瞬,旋即飞走。我很想去草木丰茂的地方追逐它们,却好像是生命力被压抑住了一样——虽然看上去只是我带着小孩,不方便去那样的地方或是做自己的事情——于是连停都很少停,只是往前骑。只在看到天边的云实在好看时,才停下来,短暂地停留一会。看它在没几分钟的时间里,从一段低平的积雨云上升为一团明亮巨大的浓积云,又很快从云头坍塌下去,变得模糊,最后散成一块普通晦暗的大云。
车很快离开我最熟悉的一段,去到陌生一点的村子。说陌生,其实也是少年时每次上学放学都要经过的,这些年再看到,却总觉得很陌生了。过去的楼房或平房坐落在它们原先的地方,一些已经荒弃,一些里面还住着老人。这些面孔,我过去上学时见过很多遍,如今见了也觉得熟悉,仿佛依稀能从中瞧见过去的影子,只是已完全不能再记省到底是过去哪些人,或该如何称呼。好像害怕被人发现有人窥见其中的衰败,又好像一种羞赧,害怕被人认出此刻这载着小孩从路上经过的人,就是过去常常从这里走过去上学的孩子,虽然明白这只是我一个人的胡乱思想,也总是匆匆而过。再往前是一段山坡,道旁草木暧暧,几乎要遮到人的身上来,偶有人在路边空地上见缝插针地种一点蔬菜,一行大豆,或一架冬瓜。无人水塘边,遥远一角种着一小片莲藕,这时节藕花已将开尽,莲蓬结在水面上,也无人采摘。暮色渐渐笼上,将四围小山的阴影投到水塘四角,中间是那朵已坍塌下来的巨大白云,在暗暗波面上,映出一片雪白。在这样看似通达实又荒寂的路上走着,心里很快觉得害怕,却不敢在小孩面前表露出来,因为显得太胆小了,因此总是骑不了多远即回头。有时时间尚早,到了村口,天还远远未黑,我们便朝另一个方向接着骑去,在那里另外再找一条路,进去短暂流连一会儿。
这是久不在家乡生活的人的疏离,便是在生命起初待得最长久、最熟悉的地方,也已有了异乡感。这并不是说,我在北京已有了归属感,事实上,在北京的第十年,北京于我仍只有自己日日打扫和身处其中的那一小块地方是有真实感的。这种情感的内缩在这几年随着身处的世界的变化而愈益明显。詹姆斯·伍德在《世俗的无家可归》里写过一种类似的情感,在离开英国去往美国生活多年后,在美国的生活已成为他人生的主要现实,但他心里却对那里始终没有真正的联结,只有努力维持的距离,“没有过往”,“疏离感的轻薄面纱盖住了所有的一切”。然而等他回到英国时,才发现“同样的轻薄面纱也盖住了所有一切”,英国的现实对他而言已消失在记忆中,回英国的感觉像是试穿过去的结婚礼服,看看它是否还合身。
他用“世俗的无家可归”或“离家不归”来概括这种在现代十分常见的个人与家园分离。在其中,个体与家园间维系的纽带松开了,也许欢喜也许忧伤,也许暂时也许永远。它不是流亡式的放逐或无家可归,而是更轻松、更日常、更像是个人自由选择的离家不归或偶尔回归,可能持续不断地进行。不过,相较于詹姆斯这种更为清浅的离家不归(尽管它也包含了失去在其中),我的感情也许更接近于后来我所看到的法国作家迪迪埃·埃里蓬在《回归故里》中所表达的情感。那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儿子(同时因为同性恋的身份而感受到双重的格格不入)用尽全力脱离原本的社会阶层后,再回顾来路时所感觉到的割裂的悲哀与刺痛。由学校和知识为代表的上层阶級的行为范式,与他自身所处的平民阶层的行为范式是如此不同,以至于作为条件,他必须和他的故地,也就是他过去所处的世界,一点一点地分离开来,乃至完全逃离。不被排斥出努力想融入的那个系统,就意味着要与自己原本的世界分离。“保持这两种社会身份、相安无事地同时归属于这两个世界,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
这种与原本更低的阶层分离的痛苦,更接近于我们这一代农村人通过读书离开家乡的经历。如果不是过去的世界仍如此落后和不断萧条,也许我也便能拥有更为清澈的离家不归的情感。不过在那时,我并未清晰意识到这点,只是感觉到一种朦胧的安慰、疏离、寂寞、悲哀或伤痛的情感,它们时时交错着袭来。这感觉在每次回家过程中都会出现,虽然并非无时无刻:看着这一小片天地中悄然变化的情状,或是遇到使我感觉伤心的事时,我常常感到这种自身与家园之间的悬置,那即是我会回到这里,其中感到我已经成为一个不属于这里的人。在那个黄昏我想到,虽然不能将北京当作情感的依归之地,随着时间无可置疑地过去,我在那里生活的年份却终将(甚至很快)会超过我曾在这里生活过的十八年。
这感情无法向在我车前踏板上安装的小座椅上坐着的小孩吐露,他只是在我双手和身体环拥出的那一小块空间里,感到很安全地坐着,对着路边的构树果感着兴趣,无论去到哪里,总要留意路边有没有构树,看到一棵树上结了红红的果子,便要求我无论去或回的路上,总有一次要停下来,给他折一枝果子。于是我停好车,穿过草丛,去为他折一枝最大最红的果子,给他擎在手中。我常常在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构树下折果子,那旁边有一户人家,是村子里为数不多仍有人住的人家之一。有一天屋子里灯已经亮起来,一个老人走到门前和他们说话,于是那家的人也走到场基上来,见我们在旁边,也走过来看。是一个妈妈和一个小女孩,她们看了我们一眼,见我们所做的是如此平淡而又有点奇怪的事,便又走了回去。许多燕子盘旋在旁边另一间空屋的场基上,在日落前捉飞虫吃。因为那无法再得的失落,这盘旋的燕子使我感到嫉妒,仿佛它们理应盘旋在我家的屋后、门前一样。
回去路上,已有吃过晚饭的人从家门走出来,在路旁散步或聊天,消磨天黑前最后一段时光。有一次我听到三个妇女议论我们:“带小伢出来兜风的。”明显是对这不太常出现在附近的面孔产生了好奇。很快到村口,总能看见上面大坝子和本村的人,聚在二坝埂的水泥桥上聊天。我从来也没见过我的父母在这个时候坐在这里聊过一次天,好像他们总有永远也忙不完的事情似的。不过,我知道那背后更深的原因,那即是已在城市生活过几年的爸爸,感觉到自己已和他们不大相同。等回到家门前,夕阳已快落下去,蝉在树上集体发出这一日最响亮的躁鸣。妈妈早已把门窗全都关上,防止蚊蠓飞进家里,又一一给房间、洗澡间点上蚊香(我们洗澡时,就常常会不小心踩到放在洗澡间外间地上的蚊香盘,烫得发出一声嗷叫)。看到太阳把西边的云染得一片金黄明红,我赶紧拿起相机,爬到楼上,匆匆拍下这一日最后的光明。楼下妈妈呼喊吃饭。而后是吃饭、洗澡。我们总在爸妈房间一个四方的宜家小矮桌上吃饭,那是姐姐不要了从城市里带回来的。爸爸在田里做事,回来洗过澡后,就把房间空调打开,坐到床上看电视,余下一切归妈妈做。她不敢劳动他做家里的事情,无论自己要不要下田,都尽量独力做完家里所有事情,除非是要爸爸搭把手的。我和她一起端菜、端饭、拿筷子、拿酒杯,跑几趟把所有东西拿到房间,然后我靠着墙,在那边小板凳上坐下来,为他们从身边泡酒的坛子里各舀出一碗已泡出琥珀色的酒。匆匆吃完,我便回到自己房间里,阻止我跟父母长时间待在一起的,是电视里抗日电视剧或新闻节目的声音,小孩却珍惜这一日难得可以多看电视的时间,即便放的是他不感兴趣的东西(他说:“公公老是看打枪!”),也总要在洗完澡后,去公公阿婆的房间再待上大半个小时。出于疲倦,以及想让小孩和祖辈亲近的愿望,我躺在床上,任由他在那边待到他不想待了为止。
白天在房间,有好多次,在陪小孩写画的间隙,我躺在床上,或是地上,听见白头鹎在门口唱歌的声音。一声接一声不歇地,一唱唱好一会儿。春天在北京的公园追寻过许多次白头鹎的歌声,现在这声音我已经很熟悉了。白头鹎的歌声清脆明亮,是很动听的。我知道它们是在门口一棵桃树上。那里两棵桃树,都是爸爸在前几年种下的,一棵上结了桃子,爸爸学人家果园套了袋子,一个个长得很大很好,是晚桃品种,此时还没有熟,另一棵却不知为何没套,也结满了桃子,只是个头小,许多已被入夏以来陆续的雨水打得这里黑一块那里黑一块,看起来不太值钱的样子。家里没有人摘吃,于是有好几次,我站在灶屋门口,看见白头鹎们鸣叫着飞来,停在树上啄桃子吃。不过有一次,我听见声音,出来看时,却发现树上停的是几只领雀嘴鹎,而不是白头鹎。翅膀也是美丽的苔绿,只是头黑黑的,不像白头鹎的后枕上有一片漂亮的白。它们看见我,就倏地从桃树上飞走,落到隔壁庭中玉兰树上,在那无人的院中玩了一会,又飞到前面人家屋边一棵大枫杨树上,继续发出明亮的歌唱。
偶尔白天大云坍塌,也会带来一场夏日的暴雨。下雨使人感到快乐,不仅因为下雨会凉快,也因为这意味着爸爸这一天可以不用去给田里打水,而把灌水的事交给老天。每一场暴雨开始后不久,家里都会停电,有时是不知道自家哪里并线了(几天之后,是妈妈发现外面有一根电线断了,让爸爸去处理,他只是用他那一贯糊弄生活的态度把那截电线挑起来挂到竹篙上,不过后来下雨时就不再停电了),有时则是村子不知何处的电线在暴雨中发生了问题。我们把门打开,让外面的空气进到房间,心里倒也并不着急,电大概终归是会来的,只是这问题的解决要留到暴雨之后,到那时再来烦恼、探看。夏日的白天总是很长,黑夜不会那么快降临。暴雨过后,大地上暂时充满潮湿凉爽的空气,这时候倘若骑车出去,流动的空气将人裹拂其中,是意想不到的舒适。有一天,雨刚刚停下后,小孩跑到门前塘埂上的菜园里去摘菜,我跟在后面,只见隔着水塘,对面领雀嘴鹎曾停留的那棵枫杨树上,一大群燕子正在树顶不断盘旋。这棵树在我小的时候就已经存在,那时已经是一棵大树,如今更其庞大,舒展接近于一团绿云。暴雨带来的风尚未停息,把树枝吹得摇摆不定,燕子就在这气流中不断颤颤翻飞着,一边发出尖锐的鸣声,大约是在捉随着雨停后飞起的蚊蟲吃。那场景十分美丽,使我感到一种仿佛从过去到现在的召唤,燕子翔集在枫杨树顶的情形,是那么多天里真正使我感到乡村生活中有活力的少数片段之一。
除我回来后的头一两天,后来田里妈妈的事已做完,只剩下爸爸每天轮流打水、修田埂、打除草剂之类,她不再下田,但家里终日的事已足使她忙得团团转。上午灶屋里已经火热,一座黑色的旧电风扇开着,吹着些有气无力的风,妈妈淌着汗,十点多快十一点就开始烧中饭。在那之前,她已经做了一日中的许多事情,洗衣服(因为爸爸的衣服带泥,而不能用洗衣机洗,要自己在洗澡间一件一件用手搓过之后再机洗),去菜园摘菜,把爸爸种的许多已经长老而无人吃的玉米全都掰回来,把玉米秆子砍倒,拖回来晒干。这玉米没有打过农药,长得不怎么样,许多都生了虫,妈妈煮一大锅,白天放在台子上,我们也都不想吃,余下的也就不再煮,都收进了冰箱里。把还嫩的豇豆摘回,在阴地里晾一晾,塞进家里买酒留存下的塑料大瓶里,加盐和凉白开做腌豇豆。拔草,砍草,就连奶奶去世后,一年中只叔叔回来那几天会有人住的旧屋前长出的高高的蒿草,她也在某个清晨拿镰刀去砍尽了,并在之后毫无意外地被我责备了一番。一日三餐,她要去外公外婆家送饭,并赶在这时间里抢着给他们洗碗、洗抹布、洗衣服、扫地拖地、清洗马桶。这几年,几个阿姨陆续从乡下搬到县城,因为孙子们上学要去县里,为了照顾小孩子们,便跟着一起搬去儿子家,或是和儿子媳妇住在一起,或是儿子媳妇在外打工,自己单独在县城替他们照顾小孩。只有三阿姨和妈妈,跟着女儿去了外面城市,离得远,不在身边。去年下半年,外公外婆在县城轮流住了半年,终因外公的脾气太差,而又送了回来。从那以后,外公外婆的生活基本上就靠几个阿姨轮流每隔几天从县城回来一次,给他们做一点饭、洗一下衣服来照顾。舅舅家在外婆家上面,不过百来米远,但舅舅显然认为这个事情跟他无关,于是阿姨们每每轮流着回来,当妈妈从姐姐家回来时,这件事情就完全交给妈妈来办。
每天吃中饭前,妈妈去给外公外婆送饭,把炒的菜小心搛两个碟子,炖的汤用一只大碗装着,上面蒙上她在拼多多上买的保鲜膜袋,叠架在大篮子里,然后挽着篮子走上去。对于她的这种行为,爸爸保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他自然不会阻拦她在一年中不多的回来的日子里一日三餐侍奉年迈的父母,对于一切逢年过节应给长辈的钱物也不短缺,但又仿佛总有点看不惯的样子,因为我的外公自私、胆怯,偏爱子女到昏聩的程度,实在算不上一个令人尊敬的人,而妈妈恰恰属于无论如何付出也不会得到怜爱的那几个之一,爸爸一贯以来又觉得只有他的亲属是最好的。他对妈妈把家里一切好吃的挑出来带给外公外婆,只给他留下不太好的食物的做法感到不满(据说只是因为我带着孩子回来了,这几天家里才吃得好一点,平常只有他和妈妈在家时,妈妈常常只炒一点素菜,荤菜做一点,都挑出来给外公外婆去了),却又不和妈妈说,只在妈妈上去时在我面前仿佛不经意地说两句。但妈妈不用说是知道的,她每出门前,因此总好像有点不安,嘱咐我们先吃饭,说自己马上就回来了。我在房间不动,等她回来一起吃,爸爸在他的房间一边看电视一边等着,心里不知是否有所不满。他又说阿姨们无论何时来,妈妈都要把家里一切能给她们的东西,从坛子里的腌菜到姐姐们买回来的塑料袋,都要让她们带一点走,而在妈妈那里,则是爸爸看不起她的姐妹。我听着他们各自向我抱怨,口里只能安慰,心里想的却是家里到底是如何贫穷,才会使他们对这么小的事情斤斤计较到如此地步?一面越发给他们买些吃的用的回来,一面感到这无异于杯水车薪,爸爸那从未曾说出口的真正希望,是女儿们不可能的发财。
虽然只有几百米的路,正午骄阳似火,走进那样的太阳里,实在还是使人感到畏惧。有两次我看不下去,说我骑电瓶车上去,妈妈百般推却之后(她推却自有她的理由,除了心疼她的女儿之外,害怕爸爸见是我冒着大太阳送上去,心里肯定要不高兴也是原因之一;而我之所以没有在一开始就说,自然也是因为知道如果是我送上去,爸爸发现了难免要怪妈妈),最后同意让我一试。我先试着骑车载她,那车却太小了,她拿着篮子坐不下,于是我试着独自带篮子上去,那篮子却又很难平衡地挂在车龙头上,没骑几步,碗里的汤已洒了些在地上,妈妈在后面心疼得大叫起来:“你下来你下来!我汤泼完的了!我讲我上去送你非要你上去送!”我只好停下来,感叹她的夸张,同时却只能理解她的这种夸张,重新把篮子交给她,看她在毒日下的水泥路上走到大坝子去。拿到篮子,她就又恢复了镇定,安慰我说:“我走上去快得很,马上就下来的。”
事实当然不是如此,常常她要过好一会儿才下来。因为妈妈在一切地方,无论是女儿家、自己家,还是父母家,所有习惯都是要尽可能地把一切都打理好,无论时间是否短暂。于是她抢在这时间里给父母做卫生,又害怕耽搁的时间太久,爸爸在家要不高兴(不管他是不是真的会不高兴),因此总像打仗一样。等妈妈回来后,我们就一起在房间吃饭。午饭后,当过了一两个小时,我偶然走出房间,却常常发现她仍然没有休息,而正坐在后门口的楼梯上,在那里稍微的风凉之处(小时候夏天,家里没有风扇,我们总是坐在那里给家里剥豆子、掐山芋梗子,或者乘风凉)剥花生。春天时叔叔回家,从外地带回两大蛇皮袋新花生,爸爸丢在那里没有管,渐渐都变成干花生了,于是她每天趁着闲下来的工夫,在那里一点一点剥,想看看能不能剥完了让镇上油坊帮忙榨成油。这么多花生,光吃是吃不完的。我要走过去怪她,问她为何就不能让自己歇一下,知道她不会听,只有蹲下来和她一起剥一会儿。她每天倒一点出来剥,剥好的花生米,都倒进姐姐带回来的一些小手提纸袋里收起来。过了几天,有一天早上她问人借了一辆老年四轮电瓶车,自己去镇上问了问(害怕油坊的人不认识我,将直接拒绝我),结果油坊说榨菜籽和花生的机器不一样,不能帮榨。在那之后,但凡有要好的邻居或亲戚来,她总要让人倒一袋没剥的花生带回去吃,但白日只要得一点空闲,就还是坐在那里剥花生。
她在心里盘算着该在哪一天让我去看外公外婆最合适,既不使爸爸觉得她过于指使,又不使外公外婆觉得我过于怠慢。虽然外家离得这样近,走上去不过十来分钟,倘若一回来就让我带着小孩上去看他们,爸爸无疑要不高兴。虽然没有禁止过,但他是宁愿我们回来不要去外家的,一说起去外公外婆家,他就常要提起几年前我抱孩子上去,回来时想让阿姨騎电瓶车送我,结果被外公在背后骂的故事,说:“上去干么事哎!有什么好去的!”当然,在奶奶尚未去世前,他也并不强迫我们多去看就住在屋后的奶奶,知道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感情,每次回来,只要去打一下招呼就可以了,到后来奶奶因为失聪和阿尔茨海默病完全无法沟通时,我们去奶奶家的时间就更短了,但那时我们却常常去给奶奶送饭。大约从念高中时起,爸爸不再管我和妹妹的事情,我们花费了漫长的时间,一点一点挣破得些男权社会套在身上的铁壳,到回来时,还是会因为从小对他的威严的害怕,而在他面前较平常显得更为驯服和软弱一些——虽然现在他已经极少再对我发火,有时候我且已经成为那个会在他面前发火的人了。但更多时候,是我在他和在这家庭中从来地位较低的妈妈之间转圜着,努力不引起他任何可能针对妈妈的情绪。因为爸爸的这种不赞同,我在内心中比平常要更退缩一点,虽然我对外公外婆也并没有什么深刻的感情,这感情和对奶奶的一样,是因为从小几乎没有感受过来自祖辈的关怀而淡薄至此,不过,在外公和外婆之间,还是存在着差别,倘若说从懂事时起,我就能明确感知到外公对我们的视若无物,在外婆那里,我还曾感受过一些温柔的、共同相处的时间,因此,对外婆的感情要深过对外公的。如果不是我在内心也不大愿去主动探看的这种退缩,我大概会在更早一天提出去看外公外婆,但因为爸爸,也许还要加上炎热的天气,不济的精神,我在回来的头两天里并没有主动提出去看外公外婆。到了第二天傍晚,爸爸在田里还没回来,妈妈对我说:
“明朝下昼晚你带宝宝上去看下家爹家奶,我跟家爹家奶讲得你明朝上来看他们,我在我钱包里拿两百块钱给你,你到时候拿上去给他们。”
逢年过节,如果我没有回家而妈妈回来,我是会给妈妈手机上转一点钱,让她带给外公外婆的。这样做除了能给外公外婆点零花之外,也可以让妈妈开心,这样她在父母面前能够挽回一部分由丈夫损失的情感,因为她的女儿还喜欢外公外婆。她知道现在年轻人都不取现钱了,常常在我回来时主动悄悄替我备好现金。我心里微微震动,一面为自己竟拖着没有主动提出去看外公外婆,一面感到妈妈毕竟是要为我做出符合她的安排,于是说:“好的,那我微信给你发个红包。”
她说:“我不要你把钱给我,我要你打钱给我干么事!一年到头打那么多钱了!”
其实一年中拢共也没有给过几个钱,但在乡下的观念里,外孙女这种泼出去的水自然是不太需要常给外公外婆钱的,妈妈觉到不安,又觉得我平常已经给她和爸爸花了不少钱,不该再让我多花费一丁点,于是试图用自己好不容易攒的一点个人的钱来把它弥缝上。
我往她微信中转了两百块钱,说:“我自己给家爹家奶钱,难道还要你出钱吗?”
第二天傍晚,我带小孩去大坝子上看家爹爹家奶奶。我和小孩骑车上去,比妈妈走得快,到外家门口时,妈妈还没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