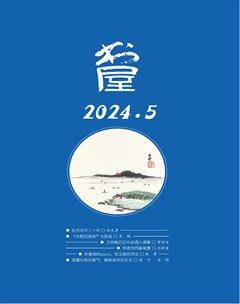“少见的奇才”
白先勇1958年开始发表小说,作品渐多,声名渐显。1968年,余光中主编《现代文学》杂志,把他的“照相摆上封面”。1971年,他出版短篇小说集《台北人》,内附1969年夏志清所写论他作品的长文。文中称他“是当代短篇小说家中少见的奇才”,拿他和鲁迅、张爱玲等相提并论。白先勇的台湾大学同学欧阳子用水磨调般的功夫,细读细评白先勇《台北人》中篇章,成书《王谢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析与索引》,于1976年出版。这十多年间,小说集一再面世,读者众多,白先勇声名鹊起,愈来愈为各地文学界所推崇。1977年长篇小说《孽子》开始连载(1983年出版单行本),题材新颖,惊动文化界,评论纷纷,白先勇享誉更隆。长、短篇小说有多种语言译本,他进军欧美文坛。
白先勇不甘心只用文字吸引读者,而向戏剧和电影界发展。根据他短篇小说《游园惊梦》(1966)制作的多媒体话剧1982年首演,先后让台北、香港、广州等地的“白迷”增添了声色的艺术享受,希望多读到白氏小说的各地文友,欣赏演出之际,戏称他的跨界是一种“不务正业”。早期的短篇小说《孽子》,以及其后的两个短篇《夜曲》(1979)、《骨灰》(1986)之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小说家白先勇的业务确实有转变,他“多媒体”起来了。其多篇小说如《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玉卿嫂》《孤恋花》以及《孽子》都先后被搬上银幕,而白先勇往往参与相关制作。
昆曲《游园惊梦》萦回一甲子
“不务正业”的最大制作——昆曲青春版《牡丹亭》2004年登上戏台。这个“青春版”从对昆曲的惊艳到青春版《牡丹亭》的首演,其酝酿、筹备、苦干,白先勇前后足足用了近六十年的光阴。杜甫“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白先勇(1937年出生)九岁时在上海初看昆曲《牡丹亭》的折子戏《游园惊梦》,心即动,将近一个甲子的岁月里,闭目时耳边常常响起“那段美得凄凉”的《皂罗袍》。他这样记述小说《游园惊梦》的写作情景:
那时我从台湾带了一些七十八转的唱片到美国,其中便有一张橘色女王唱片是梅兰芳的《游园惊梦》,我一边写小说《游园惊梦》,一边聆听梅兰芳的唱片。唱到《皂罗袍》那一段:“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笙箫管笛,婉转缠绵,幽幽扬扬,听得我整个心都又浮了起来,一时魂飞天外,越过南京,越过秦淮河——我幼年去过的地方,于是便写下《游园惊梦》,描述秦淮河畔昆曲名伶蓝田玉一生起伏的命运。
白先勇认为好的文学作品离不开“情”与“美”两个元素。让他难忘一个甲子的《皂罗袍》,正有“良辰美景”之美,以及“奈何天”之情。少女杜丽娘怀春,对着美景,却无情人与她共赏,本是乐事,却无情人与她同乐,是以郁郁寡欢。美景与愁情构成对比,有如盛与衰、生与死等种种人生情景,正是文学艺术感人动人的基因。
今年是青春版《牡丹亭》演出二十周年庆祝之年,一本纪念性的大书在阳春三月出版,白先勇在此书的三万多字的序中,缕述他如何与昆曲结了一辈子的缘。1987年,他在上海观看昆曲演出大受感动:“我们民族的文化瑰宝‘百戏之祖’昆曲居然重返舞台大放光芒。这样了不起的艺术一定不能任由其衰微下去,我当时心中如此思索。佛家动心起念,隐隐间我已起了扶持昆曲、兴灭继绝的念头。”2000年在“家中心脏病发,命悬一线,……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我一心悬念的竟还是昆曲”。大约两年后,白先勇和台北、香港的朋友讨论如何推广昆曲,如何纾解当前昆曲的危机。他要守正创新地制作一部青春版的昆曲《牡丹亭》。
青春版《牡丹亭》:复兴昆曲、迷醉四方
白先勇如同好莱坞星探,相中了大陆的昆曲老少演员、导演,“招兵买马”,殚精竭虑,制订整个演出的风格和方案,包括服饰、音乐、舞美等的设计。汤显祖的《牡丹亭》长达五十五折,青春版《牡丹亭》自然不可能全部演出。白先勇成立“劇本改编小组”,决定对原剧“只删不改”,“剧本磨了五个月终于成形”。2003年4月,在他敦促之下,青春版《牡丹亭》正式开排。由于白先勇文艺的精致思想和完美要求,演员经过长时间“魔鬼营式的训练”,一年后,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正式上演。
《牡丹亭》这部戏曲“歌颂青春、歌颂爱情、歌颂生命”,如今加上“青春版”的各种青春元素、青春色彩,果然大受欢迎。白先勇不改《牡丹亭》的文字,但剧本做了一些微调:一是兼重男女主角柳梦梅和杜丽娘的戏份;二是《惊梦》一折演到两情相悦、鱼水交欢的时候,向来的演出十分收敛拘谨、轻轻带过,白先勇让青春版《牡丹亭》“放宽一些,让青年男女的热情表现出来”。如此这般,我认为这演出的剧本,可看作白先勇一个小小的“再创作”。白先勇认为“台北首演成功意义重大,影响扩大到海峡两岸及香港的文化圈,开启了昆曲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