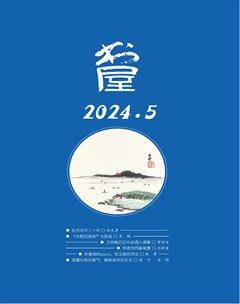“合肥四姐妹”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出生于二十世纪早期的合肥,是清末淮军主将、两广总督署直隶总督张树声的曾孙女。她们的父亲张武龄(1889—1938),别号冀牗,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毕生致力于民族教育的现代化,兴办苏州市乐益女子中学;她们的母亲陆英,是来自扬州的大家闺秀,为两淮盐运司陆静溪之女。张家经历了两次搬迁,先到上海,之后迁居到苏州的九如巷。张武龄给四个女儿的名字中都带上了“儿”,象征人的两条腿,意味着女孩子要走出家门,怀有更大的人生格局。
在从合肥迁移到上海、苏州,后来又到北京、台湾乃至异国他乡的过程中,四姐妹由于受到父母喜爱戏曲的影响,一直都致力于昆曲的学习、表演和传承事业,但其影响力不止于此。
大姐张元和大学时代就喜爱昆曲,后与四妹张充和一起随苏州的昆曲名师学习,男女角色均可扮演。她和昆曲小生顾传玠因昆曲结缘,突破世俗对于戏曲演员的歧视,与顾结为秦晋之好。顾传玠天分极高,嗓音、扮相皆为上乘,同时擅长吹笛,年纪轻轻就在表演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以至于梅兰芳作为梨园前辈,两次邀请他合作。非常可惜的是,顾传玠因为昆曲演员地位不高、收入微薄等原因告别了昆曲舞台,转行从商,张元和却从票友慢慢成长为度曲专家,并经常登台表演,直到八九十岁仍可以演出。二姐张允和沿袭童年时代的昆曲基本功,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活跃于票友圈,在新中国成立后,在伴侣周有光的支持下,更是为昆曲的传承努力奔走,不计个人得失。三姐张兆和童年时代也学过昆曲,学生时代经常参加学校的戏剧演出,对于昆曲的浸染虽然不如姐妹们深入,但是一直支持伴侣沈从文的写作和对古代服饰文化的研究,整理其遗作。四妹张充和青年时在苏州养病期间与大姐元和一起深入学习昆曲,后虽远嫁美国,在大洋彼岸仍坚持昆曲的演出、教学等工作。她的伴侣傅汉思受到她的影响,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罗曼语文学转而研究汉语言文学,取得了丰硕成果。
四姐妹在将自己的学识和才华联结到更广阔舞台的同时,与世界各地的文化人结下深厚情誼,并和他们的伴侣顾传玠、周有光、沈从文、傅汉思一起,致力于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扬。
四姐妹的母亲陆英是一位从传统女性向现代女性过渡的典型。她来自扬州的一个大家族,性情敦厚,恪守妻职母职,擅长治家,负责主持张氏家族的寿宴、丧事、嫁娶等各种大型活动。作为传统女性,她前后生育了十四个子女,但是,跟她的婆婆一代人不同,陆英识文断字,已经具备一些新式女性的特点。比如,她喜爱看戏曲表演,在照顾婆婆之余,如果有梅兰芳或尚小云的演出,就会从家里“悄悄溜出去,到戏院事先定好的包厢里好好欣赏一番” 。这说明她在相夫教子的同时,有自己的精神追求。她还在家中发起了“保姆识字运动”,希望帮助劳动妇女更好地主宰自己的命运。
他们的父亲张武龄,原名绳进,字武龄。“绳进”这个名字来自《诗经》“绳其祖武”,意思是沿着祖宗的足迹前进。张武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读书上,从古代经典、戏曲、史书到白话文的小说、随笔、译作等,广为涉猎,还订阅了超过二十种报纸。这种超脱功利的读书让他有了更宽广的视野,对国家民族有了更强烈的责任感。张武龄给自己起了个别号“冀牖”,意思是等待着光从窗格子中透入,有“开启民智”的意味。他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这一社会理想,成为知行合一的典范。张武龄将原本用于孩子出国留学的钱省下来,创办了苏州乐益女子中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掌握知识、走出家门、贡献社会提供了机会。值得一提的是,他办学校之心不在营利,每年提供十分之一的名额,招收免费生,以便贫家女儿入学。这么高的比例,在江浙一带罕见。他办学的理念、教育救国的责任感、对大同世界的向往体现在他创作的校歌歌词中:“乐土是吴中,开化早,文明隆。泰伯虞仲,孝友仁让,化俗久成风。宅校斯土,讲肄弦咏,多士乐融融。愿吾同校,益人益己,与世进大同。”
张武龄本人对于昆曲的喜爱源于少年时看《红楼梦》,从书中得知有昆曲这一剧种,非常痴迷,于是读了大量的昆曲剧本,他曾跟子女说:“昆曲的文辞是集中历代中国韵文的大成,留下的剧本既丰富,又精美,是其他剧种望尘莫及的,昆曲的舞蹈(动的叫身段,静的叫亮相)是中国活的雕塑艺术,尤其在亮相中表现更为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