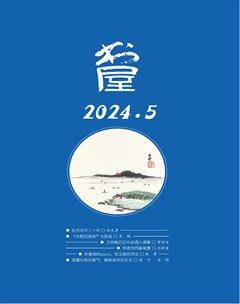2020年12月,学苑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当代史学专家王钟翰先生的《甲丁日记》手稿,因日记起于1954年而迄于1957年,1954年为旧历甲午年,1957年为丁酉年,取头尾两年天干二字,名为“甲丁”。
王钟翰(1913—2007),湖南东安人,长沙雅礼中学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4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两年,归国后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和中央民族学院,为研治清史与氏族史的著名学者,著作有《清史杂考》《中国民族史》《满族史研究集》等。
王钟翰一生嗜酒,年轻时就因酒量好而广为人知,《光明日报》曾以《王钟翰:酒史一生》为题刊发长文,文中提及王钟翰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的一件趣事:
但他年轻时酒量极好,有过“饮酒败倭寇”的一席佳话:1937年,王钟翰还是燕京大学历史系的一名学生,因为为学校做些杂事有些收入,所以隔三差〔岔〕五就请一些同学好友进酒馆“改善伙食”。久而久之,他酒量大的名声在燕大传开了。当时太平洋战争还未爆发,日本宪兵队队长华田碍于燕大教务处处长司徒雷登的面子,无法明目张胆地进校搜查抗日学生,但也经常找各种理由到燕大滋事。一次,华田要与学校的教职员工斗酒,王钟翰被同学老师推荐为代表,慷慨“应战”。十瓶啤酒过后,华田醉倒在酒桌底下,王钟翰却没有丝毫醉意,周围旁观的师长同学兴奋不已,连声喝彩。很快,一家报纸以《王钟翰怒斗倭寇》为题报道了此事。
此事灭敌志氣而长我威风,在当时的北平文史学界传颂一时,王钟翰也引以为毕生快事。
中年以后,王钟翰仍喜欢小酌几杯,《甲丁日记》中便不时有关于酒的记载。以人论,或师友聚会,或知己对饮,或一人独酌;以酒论,或白酒,或黄酒,或红酒;下酒菜或丰或俭;酒桌话题或学术或家常。在王钟翰笔下,都醰醰有味,风致悠然。
物质生活不充裕的年代,即便是大学教授,平时生活也比较简素,年节和生日便成了最好的宴饮由头,王钟翰日记中半数以上的酒人酒事都与此相关。
最早一则关于饮酒的记录是1954年10月17日的日记:“四点多潘作翰(运之之长子,师之外孙也)来催,并云今日乃伊外祖母之六十七寿辰也。略整衣冠而出,并携苹果酱一瓶,以作寿礼,因师母爱吃甜的之故。到时,汪、凌等正在里间饮宴,宴后坐谈,七点又设一席,且饮且谈,八点散席,又坐谈一小时,然后兴辞返家。”
这里的“师”指的是王钟翰的业师邓之诚,原燕京大学资深史学教授,当时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住在北大东门外成府村的蒋家胡同二号,即今北京大学法学院所在地。而此时的王钟翰方调至中央民族学院任教,但因妻子涂荫松在北大医院工作,所以安家在北大的中关园宿舍,自己每周骑自行车去民院上班,工作日住在学校,周末或有事时回家。中关园距离成府村不远,往来便捷,王钟翰几乎每隔一两个礼拜便会登门向邓之诚请益。日记中屡以“文如师”“邓师”“文师”称之,甚至径称为“师”,是此师之区别于他师也。两人之间的关系在师门中尤为亲密,学问授受之外,日常闲谈多人物月旦、时事品评,言语且肆无忌惮。此外,两人私交甚笃,一则日记中提到的邓之诚发妻庄宛如做寿,遣外孙邀王钟翰赴宴即是一例。值得一提的是,王钟翰日记中所说的当日乃师母“六十七寿辰”实为误记,邓之诚当日日记称“九月二十一日十月十七日星期晴暄,内子七十生日,子女来热闹一日。汪太初来,钟翰来。”邓之诚此时妻妾共处,大约不易请外客为老妻庆祝普通生日,七十整寿才值得大张旗鼓地宴请宾客,显然也更符合实际情形。祝寿者且基本是自家子女孙辈,外客只汪太初和王钟翰二人,妇人之地位如此。至于邓之诚自己的生日,自然要隆重得多,王钟翰1955年11月28日的日记,便记录了邓之诚六十九岁生日时高朋满座、旨酒佳肴的热闹场面:“五点半赴文如师之宴,六十九寿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