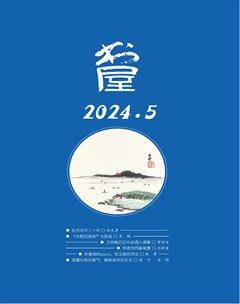对于作品与作者,一般情况下,大多数人都是先读其书后识其人的。然而,对于广陵书社新出版的这部《论语今解》,我却是先识其作者,而后才读其书的。毫不讳言,正因为对于该书的作者唐翼明先生怀有无限的敬意与钦佩,我才兴致勃勃地花费了大概一月时光,从头至尾读完了他的《论语今解》。
《论语今解》算得上一本大部头作品,全书六百四十一页,五十万字,囊括了《论语》全本,同时配以注释、大意和导读。该书封底印着“底本可靠,名家诠解,观照现实”十二个大字,可谓“所言不虚”。就我而言,关于这部书的阅读感受,可以套用《论语》开篇的话,那就是“不亦说乎”“不亦乐乎”。作为中国人的精神原乡和文化“圣经”,《论语》是一部中國人人必读之书。钱穆说,读《论语》必兼读注。古往今来,关于《论语》的注释、译注、解读可谓汗牛充栋。再多一部《论语》注解,是否有“屋下架屋,床上施床”之嫌呢?说实话,最初拿到唐翼明先生的《论语今解》一书时,我不是没有几分这种担忧的。但最终这部书不仅没有使我失望,反而在我心中取代了其他权威注解版本长期占据着的位置。
“今”解:今之时,今之世,今之人,今之我
《论语今解》一书最突出的特点就集中在一个“今”字上。对于《论语》的二十篇、四百九十二章中的每一章,唐翼明先生都在准确的字词解释、通达的大意阐述的基础之上,做了贯通古今、横接中西的思想导读。这些导读文字文质兼美、雅俗共赏、繁简得当,充分体现了作者对《论语》的“今”解,即结合今之时、今之世、今之人、今之我四个方面,对读者阅读和理解圣贤之言进行思想观念的导引。
所谓“今之时”,就是让《论语》穿越时间阻隔,与今日之时代状况、时代精神和时代需求相对接,以今时为基准,破除《论语》中部分内容“过时”的字面意思,而取其符合人性本原的精神内涵,进而启迪于今日。比如,对于《为政》中的“子曰:‘君子不器’”一章,翼明先生在“导读”部分说,按照孔子的意思,一个人要尽可能完美,而不是仅仅成为有某种专长、能够充当一种器具的人。但是,在科技日益发达、分工日益精细的今天,这种观点显然不太现实。不过,“君子不器”在今天依然有某种警醒意义,那就是人不能“把自己培养成某种工具、某种部件,尤其不应当只是一种赚钱的工具,或者服从某种机器功能的一个部件”,人可以选择一种职业甚至终身从事该职业,“但是在精神境界上还是应当拒绝异化成职业的奴隶,或甘心为他人所役使”。再比如,对于《里仁》中的“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一章,翼明先生明确说,今天读这句话不要只看字面意思,而要注重精神。“做儿女的要心中有父母,还要体谅父母对自己的思念,不要令父母担忧。如果人在他乡,要随时跟父母联系,让父母知道自己的情况,有紧急的事能随时赶回来。”
所谓“今之世”,就是将《论语》蕴含的社会文化心理原则与当今社会的现实状况进行比较与参照,以今世为立场,承接《论语》中富于现代精神的古典价值观念,合理转化,自然演绎,进而应用于今世。比如,对于《雍也》中的“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章,翼明先生在“导读”部分说,粗野和虚华都不值得提倡,虽然文明的发展基本上是沿着由“野”到“史”这一条路前进,但走过了头或走偏了就会带来祸害。对于这种社会现象,翼明先生特别提出,如果逼不得已,要在“野”和“史”之间选择,则宁取“野”不取“史”。因为“野”近朴,“史”近伪,宁朴勿伪。再比如,《阳货》中的“子曰:‘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在“导读”部分,翼明先生指出孔子这句话值得每一个人引以为戒,尤其在今天这个网络发达的世界,网上传来传去的东西真假难辨,不可不慎思明辨。
所谓“今之人”,就是把《论语》中关于各类人特别是关于君子与小人的论述作为观人识人的视角,以今人为对象,借助《论语》的博大智慧,提醒今人,教化今人,导正今人。比如,对于《学而》中的“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一章,翼明先生在“导读”部分说这是一种经验总结,可以作为我们观察人的一种参考。没有真正仁爱之心的人,往往是这样的:“他们在有权有势的人面前表现得特别谦卑乖巧,点头哈腰,唯唯诺诺,提包打伞,唯恐不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