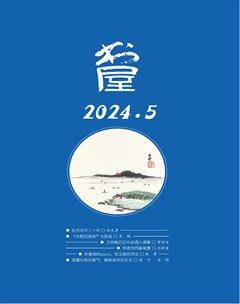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崇尚科学主义的风气,认为人文学科也应该“自然科学化”,提倡学者“莫抛心力作词人”,摒弃才子习气。同时,白话文运动也推波助澜,科学主义从专业学理上疏离文苑词林,白话文运动从语言表达上鄙弃文言雅词。这两股势力颇为强大,一时蔚为潮流,代表人物有胡适、傅斯年、李济等人。胡适晚年在美国得知陈寅恪仍在写诗,说“寅恪终不脱才子气”。傅斯年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时,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王叔岷考上他的硕士研究生,王叔岷喜欢写旧体诗词,傅斯年与他第一次见面谈话就告诫王叔岷要“洗尽才子气”。傅斯年的一贯学风是史料第一,大力寻找新史料,扩大史料的范围,宣称“史学就是史料学”。王叔岷在傅斯年主导的史语所学风的熏陶下,以校勘训诂为基础,博览群书,深入史料考据,终于跻身学术殿堂。但王叔岷成名后并没有与旧体诗词绝缘,他在左图右史、钩沉索隐之余,仍然创作旧体诗词,做性情中人,成绩斐然。
李济是中国考古学的开创者之一,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他比傅斯年更加排斥旧诗文,对人文学者题诗作对不以为然,对陈寅恪以对对子作为清华大学新生考试题目连讽带贬。陈寅恪作为世家子弟,并没有疏离儒文素业,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诗、名联、名文。若没有这批用旧式文体写的名篇佳构,特别是《海宁王先生之碑铭》《赠蒋秉南序》这样的旷世雄文,其文史大师的声名与形象可能要打折扣。
胡适、傅斯年、李济在进新学堂之前,是受过传统经史子集即四部之学的浸润熏陶的。但他们在一只脚踏进从西方引进的七科之学即文、理、法、医、农、工、商的教育体制后,对文言文、诗词骈对深恶痛绝。而另一些与傅斯年、李济有相似教育经历的学者却走了另一条道路。他们既遵守现代学术研究的学风学理,学术成果丰硕,声名卓著,又擅长写作本专业之外的文字,比那些只会写论文、做课题的学者多了一副笔墨。他们或写作诗词文赋,如陈寅恪、萧公权、缪钺、白化文等;或写作历史人物传记小说,如朱东润写《陆游传》,冯至写《杜甫传》,邓广铭写《辛弃疾传》;或写作新文学意义上的散文,如朱自清、台静农、季羡林等。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中国现代学术史梳理出两条线索:从傅斯年等人那里传承下来的依托七科之学学术框架、只有一副笔墨的学术传统;从陈寅恪等人那里传承下来的继承四部之学、兼有两副笔墨的学术传统。
这两条线索传承下来的学术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目前高等院校的科研成果评定体制偏重七科之学的专业化,大学文科老师都陷在写论文、报课题、做项目的圈子中。在高校目前流行的数字化管理模式的大环境下,已经没有余裕来顾及一个学人的另一面,高校不需要两副笔墨。旧体诗词、古文骈文写得再好,也进入不了科研管理部门的视野,不能计成果。即使鲁迅、周作人再世,凭他们的杂文、小品文,也评不上副教授、教授。但仍有一部分学者不离不弃四部之学的传统,对集部的性情文字情有独钟,两副笔墨得心应手,相得益彰。
郁龙余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师从季羡林先生,专业是印度学,是一名印地语教师。后来,他南下深圳大学任教,创立了“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是季羡林等创建的北京大学印度学的南方分蘖。他在自己专业领域纵横开拓,成果丰硕,业界自有定评。几十年来,撰写、出版了《中西文化异同论》《东方文学史》《中国印度文学比较》《中国印度诗学比较》《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论》《泰戈尔作品鉴赏辞典》《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印度卷》《季羡林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