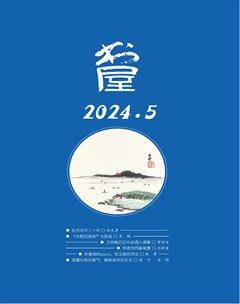一
文明的故事究竟有几种讲法?
按照时贤所云,大体我们会有两种讲法:其一,是照着讲;其二,是接着讲。通常,多数学者是会选择前者的路数来照着讲,亦步亦趋,不敢有半步的错路,最后,也必定会忘记自身原本秉有的一种可能性的步伐;而作为“接着讲”的后者,往往已是一个个体创造力的极限,得具有相当可敬的学术品格,譬如,一往无前的孤勇气概,理性缜密,能够直达高天之河汉的想象力与思维力,等等。但是,此两种讲法再高明,皆是沿袭后轴心时代的固有衣钵,属于文明旧传统、文化旧精神的精耕细作,其耕作的地界已被预先划定,至多是一棵苍老古树上的抽枝发芽。
鉴于当今时代的特殊条件,尤其是近一百年来考古挖掘的惊人成就,譬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发现的甲骨文与二十年代发现的仰韶、龙山文化遗址,二十世纪后半叶发现的甘肃大地湾与山西陶寺的太极台等,出土了数量惊人的上古陶玉铜、中古甲骨文、近古简牍帛,华夏文明早期的整体面容渐渐浮现在世人面前。此时,真正的学人若是具备足够的耐力与才能,其实还是有第三种讲法的,那就是——从头说,或重新说。
这最后一种讲法,难度极大,挑战尤多,引发的争论也往往最为激烈,因为,人们除了受观念系统的束缚,即习惯性认知的固化使得自身寸步难移之外,于穷源溯流的寻索当中,一旦涉及文明的远古与上古,就会遇到崖断路绝的局面,往往还云遮雾罩。这些学问,非但时段长,资料少,而且几乎没有任何的先例与脚踪可循,大体属于开垦拓荒的新做法、新探索。除非心中有谱、成竹在胸,掌握了最重要的工具箱与整理第一手资料的方法论,借以辨明路标与方向;否则,容易因迷境迭生,不见涯涘而生望洋之慨,最终不得不返回自己熟悉的旧地貌,重操旧业。
当今中国的学人里面,上海的张远山先生在此一领域堪称一骑绝尘,借助考古学与遗传学的新学问、新方法,加上他原本就悟力惊人、学达性天,兼十分熟悉浩瀚的文献史之流变,耕耘几十年,在海量的上古图证基础之上,最终形成了《伏羲之道》《玉器之道:解密中国文明的源代码》与《青铜之道:解密华夏天帝饕餮纹》这三部奇异的著作。它们以上古陶器纹样、玉器纹样与铜器纹样为内容,建立知识学意义上的华夏图像学,他自己称之为“伏羲学”,其基本学问宗旨是:贯通华夏八千年史,复原华夏知识总图。
为此,张远山必须解密上古至中古大体六千年的华夏文化总基因(伏羲族的彩陶文化)和华夏文明源代码(黄帝族、东夷族與南蛮族的玉器文化),而最重要的则是对青铜器上面素称难解的“饕餮纹”进行解读,系统解开中古两千年铜器纹样的图法与制法。张远山十分重视“饕餮纹”的图像学意义,断定主体纹样的内涵为“天帝纹”。他认为,“饕餮纹”乃华夏图像的终极密码。
由于华夏图像系统是华夏文字系统的前身和源头,近古两千年的文字图书史与上古、中古的纹样图像史共八千年,就这样被贯通了。从此,来自殷墟的两大名词,有望成为相对稳定的公共知识:一是属于华夏文字系统的“甲骨文”,二是属于华夏图像系统的“饕餮纹”。这个知识总图里面存在着大量人迹罕至的神秘地带。譬如,甲骨文的研究者甚多,成果辉煌,但由于没有上古图像学的参照,能够解读出来的毕竟只占三分之一强;对“饕餮纹”展开深入研究的学者则更是稀少,而且研究成果乏善可陈。非但普通大众仅略知“饕餮纹”之名,莫知“饕餮纹”之义,即便如郭沫若、李泽厚这等第一流的大学者,他们对于青铜器的论述,对于“饕餮纹”,以及“夔龙纹”“夔凤纹”等纹理之鉴别,亦未见“饕餮”之真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