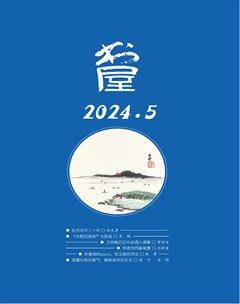驰名世界的中国古典文学泰斗孙康宜老师今年八秩寿诞,这是一件令人喜悦的乐事。孙康宜老师是耶鲁大学荣休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在学界德高望重,令人敬仰。学界能有这样的“女君子”(余秋雨先生语),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幸事。借用金耀基先生的话,乃“有缘有幸同斯世”也。
吾生也晚,2011年前后才与康宜老师相识。犹记得当时准备申请耶鲁大学的联合培养博士(这在当时还是新生事物),想拜在康宜老师门下,遂贸然去信。依稀记得康宜老师告知我耶鲁大学似乎无此先例,遂将我的信转发给他的高足、美国卫斯理安大学的王敖兄,问他是否有可能。然王兄当时刚入职,说不知如何处理这类事宜,但我也因此认识了仗义执言的王敖兄。当时校方留给我们时间极短,联合培养博士之事最后虽未办成,但康宜老师的热情襄助使我非常感动,也因此与她保持了多年的书信联系。
2014年,我以合作研究博士后的身份,到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庙岭分校访学,曾自驾美国十六州访客会友,其间赴两所学校讲学。记得抵达耶鲁时已是初秋,纽黑文层林尽染,在山路上一眼望去极其辽远且舒心。出发之前我已经给康宜老师写了邮件,表示要登门拜访。几分钟后就收到回信,并告知其在木桥镇的府上地址,我们立刻驱车前往,抵达时发现她早已站在门口等待我们到来。
康宜老师的别墅在郊区,是一栋独栋的美式别墅,周围没有什么邻居,亦无商场街道。我等栖身于水泥森林里的“亭子间”久矣,看到这样“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环境,着实令人羡慕,感慨确实是做学问的佳处。此别墅唯有康宜老师伉俪居住,这时我才第一次见到康宜老师的先生张钦次教授。钦次教授睿智又和蔼,乃是美国著名工程专家,纽约地铁7号线延伸段的总工程师。早年他在台湾中原大学读本科时,曾设计校园内钟塔,并使用至今,成为学校的标志性建筑。
那日初次见面,现在回想起来极有趣味,也印证了我之前听闻钦次老师在外是“指挥千军万马”的总工程师,在家则是一位极其周到细致的“新好男人”这一传言非虚。当时正是周末,康宜老师提议请我们到外面用餐,钦次老师笑问:“你说去哪里吃?”康宜老师说哪里都可以,钦次老师哈哈大笑说:“现在是周末,这么晚了,哪里会有营业的餐厅?”尽管十年过去了,但我仍记得康宜老师当时的表情,她无奈地双手一摊,说:“那你说怎么办?”钦次老师徐徐站起身,打开身后的电冰箱,指着冰箱里的“库存”说:“我早准备好了,在家里吃。”
后来,我和康宜老师的几位高足成为朋友之后才知道,康宜老师极少留学生在家中用餐,做饭招待我这样初次见面的“网友”,听起来更像天方夜谭。一位老兄多年后惊讶地对我说:“你胆子太大了,敢在孙老师家里吃饭!”当然我们当时也受宠若惊,内子张萱赶紧主动帮厨,钦次老师向我们介绍家中厨房一些设备的用法,而康宜老师则带我参观她的书房“潜学斋”。
先前拜读过杨柏伟君编辑的《从北山楼到潜学斋》,这是康宜老师与施蛰存先生的通信集。“潜学斋”三字是康宜老师的父亲孙裕光老先生所写。老先生一生颠沛流离,早年负笈留日,在北京教书时曾参与过地下抗日,到台湾后又因同情台湾共产党人而成为“白色恐怖”下的受难者,历经多年牢狱之苦后,在改革开放之初首访故乡天津,为天津高等教育签下了第一个中美大学交流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