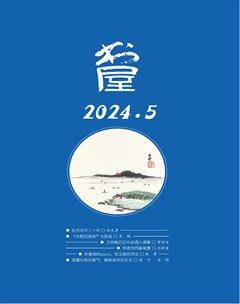听说张玉能老师(1943—2022)过世的消息后,我想起了一件往事。
2006年,还在我们这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的某教授在文艺学研究中心主持了一个“二十世纪德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基地项目,邀请张玉能、杨恒达、方维规教授和我入伙。为了督促大家各就其位,各司其职,“举头望明月,低头做课题”,他决定开一个碰头会。于是,2007年3月中旬的一天,我们聚在了一起。
会是小会,人少,加上杨老师有事没来,就我们四个人叽叽喳喳讨论了一上午。
那是我第一次见张老师。七十多岁的他专程从武汉赶来,可见他对这个课题的重视程度。而他的慈眉善目和宽音大嗓又让人一下子放松了警惕,消除了距离。于是刚聊几句,我就觉得这老头没架子,挺随和,好像另一个汪曾祺。
您还别说,拿张老师与汪老头的照片比一比,眉眼还真是差不离。当然,张老师更敦实,显然不如汪老先生飘逸。
因为要与二十世纪德国文学思想较劲,阿多诺、本雅明自然是绕不过去的。而一說起本雅明,敦实的张老师就扔出了几句沉甸甸的话:“本雅明那个aura,译法乱糟糟的。我一直想写一篇考辨文章,讲一讲aura的来龙去脉,敲定一个最好的译法。现在既然要做这个课题,似乎可以动手了。”
“写啊写啊!”“现在不写更待何时?”那个时候我们仨是不是起哄架秧子,其实我早已忘却,但我的来劲却是有据可查的。第二天,大概是想起了张老师的那番话,我便写邮件向他请教:“昨天您谈起aura一词,我很感兴趣,因为做博士论文时,采用哪种译法更合适,也曾让我颇踌躇。我最终采用的是‘灵光’之译,也在注释中略有辨析。但我不懂德文,希望早日看到您的考辨文章,以为我解惑。”
当天我就收到了张老师的回复,全信如下:
赵勇同志:
你好!
谢谢你的关心,我已经于今天早上7:00准时到达武昌,半小时以后就到家了。
认识你非常高兴,而且在一个课题组,将来见面的机会就不少了。
关于aura的中译,现在是五花八门,但是,我想有一个原则:不能没有“光”,从否定层面来看,不能有“韵”。简单地说,因为aura这个词就是与光有关的,而且“光”在西方基督教之中是重要的象征,所以,本雅明就用aura来显示传统艺术的“唯一性”和“宗教仪式性”,因此,最好译为“光晕”,译为“灵光”也可以,但是绝不能译为“灵韵”“光韵”“韵味”“神韵”等等,因为那样会产生误解。韵在中国传统文论之中是有特殊涵义的,而且其中没有任何宗教意味。我早就想写这篇考辨文章,可是深怕得罪德语的翻译者。这次,我仍然是犹豫不决的。
写下这些供你参考,你不妨也给我提供一点参考。至于请教,实在不敢当,充其量也就是互相学习、切磋。
以后多联系!
祝你万事如意!
张玉能
张老师以“同志”相称虽然略显古板(后来的邮件他一直都是称我“赵勇同志”),但他的迅速回复还是让我非常开心,于是我在邮件中说:“我当时在简单的说明中也注意到了宗教意味的问题,亦觉得‘神韵’等等太中国化和古典化。但我当时还想到的是,这一词语除宗教意味外还有美学意味,所以我使用‘灵光’,亦肯定了‘灵韵’。为什么肯定它现在已想不起来了。记得最初觉得‘灵韵’一词很别扭,是汉语语境中生造出来的,但是不是就是因为它的生造,反而有了一种神秘感?所有这些当时都没有仔细考虑,现经您指出,觉得‘灵韵’之说也是有问题的,以后我得首先改正这一点。”紧接着,我举了某学者喜欢以“灵韵”行文的例子之后继续写道:“既然问题这么多,您就更应该写这篇文章了。下面这句话说得不好请您别介意:我觉得您已到了一个不必再怕得罪人的年龄了。”
那个时候,我已把我那本已经出版的博士论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送给了张老师,为了让他一目了然,我又把书中为aura做的那个三四百字的说明性注释复制到邮件里。那个注释起头便说:“aura一词很难翻译,就笔者所见,此概念的汉语译法有韵味、光晕、灵气、灵氛、灵韵、灵光、辉光、气息、气韵、神韵、神晕、氛围、魔法……”
大概是我的鼓动还有些效果,张老师决计写这篇文章了。于是他在邮件中说:
我想可能此文涉及的问题比较多,会写得比较长。你就耐心等待吧!比如“机械复制时代”,实际上应该是“可技术复制时代”,一般人把-bar-这么一个后缀给搞掉了,这一下有可能又要扯到:我翻译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时,发现有人就是因为搞掉了这么一个后缀,把“审美可规定性”一词搞成了“审美规定性”,于是席勒的“审美教育使人达到自由”的思想变得费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