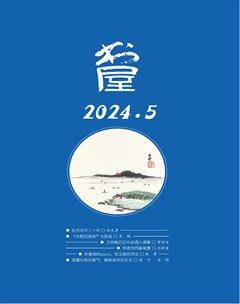“从‘西学东渐’走向‘东学西渐’”,这是两三年前耶鲁大学史特灵图书馆举办的中文典藏历史回顾展览的中心主题,也是近期坊间舆论时常关注的热门话题。2023年岁末,就《迷谷》英译本的美国传播态势与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这一课题,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生唐宁和作者苏炜展开了以下笔谈访问。
唐宁:《迷谷》英译本(The Invisible Valley)于2018年在美国出版,您认为译本在美国的传播反响如何?是否达到了出版时的预期?
苏炜: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其一,拙作长篇小说《迷谷》,无论是中文本还是英译本,都属于“小众”类的纯文学书写,都不具备“流行体质”。要想让它在美国书市引发轰动效应,像《哈利·波特》或《三体》一样得到广泛的传播反响,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所以,这也从来没有成为我这位原作者和译者温侯廷的出版预期。
其二呢,作为美国的一个小型独立出版社——“小啤酒出版社”2018年出版此书时没做什么特别的宣传。但此书甫一出版,就获得了来自各方各界的好评,在全球最大的在线读书社区Goodreads上评分高达四点零五分(满分为五分)。著名作家哈金、约翰·克劳利、帕特里克·麦克格雷斯,著名汉学家林培瑞等都对该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柯克斯书评》《出版者周刊》《图书馆杂志》等读书相关的杂志刊登出了书评。就这一角度看,《迷谷》英译本的出版所获得的反响是积极的、正面褒扬的,可以说也正是我和温侯廷(我平时习惯称他为“侯子”)所期待的,达到了我们最初的出版预期。过去五六年间,温侯廷一直在杜克大学昆山分校担任英文写作和翻译课的教职,教学成果丰硕,成为全校最受学生欢迎的杰出教师之一。最近的“反响事件”更让人惊喜——因为《迷谷》英译本在专业翻译界口碑隆盛,著名的英国利兹大学不久前(2023年秋天)专门设了一个翻译教职,正式聘请温侯廷到英国任教。目前,他已举家搬往英格兰,刚刚开始他在英语母语之地的老牌大学的英语翻译教学工作。
唐宁:中文小说在海外的流通,其实也伴随着市场行为,尤其是在文化贸易盛行的当下,小说作品的商品属性无法被忽略。您曾在过去的采访中提到,文本是重中之重,如果作品足够好,不一定非要借助声势浩大的营销。您对当下文学作品出版营销的看法是什么?您认为文学作品本身与营销手段的关系应该是什么?
苏炜:这就可以连接上你提及的我的旧话“文本是重中之重”了,上面的话题其实已经回答了你这个问题的大半,但我愿意把这个“文本”的话题继续展开。正如你前面所言,中文作品的海外流通,一定也必須与市场行为有关。市场行为,就涉及作品的商品属性。关于文学性写作,今天我们更喜欢用“创意写作”的概念。创意创意,本来最忌讳套路化。作品的原创思维,是从“0到1”,最好是要具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一份”,虽然这对于创作者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然而,对于一部翻译作品,翻译者的文本选择,是从“1到2”,则必须考虑所选择文本的市场和读者定位,也就需要认清和把握一定的“套路”了。《迷谷》文本的“独一份”,很难被归类,这既是它的特质——不落“套路”;也是它的弱项——很难被市场归类,因而影响了市场的接受度考量。所以,翻译所选择的原创作品如何“反套路”“独一份”,保证了文本具有的真实价值;但翻译文本的最终选择,又要兼顾市场“套路”,选择既独特又适应普通读者的审美期待和市场需要的文本。这里面需要探究、平衡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如何从回避、抵抗“套路”到通过认清并适应“套路”来最终突破相关“套路”,从而逐渐打开中文译作的海外市场,这是面对当下海外书市现实,中文译作推广者和运作者需要深入考量的。这是我和温侯廷在《迷谷》英译本经历各种坎坷终于出版以后的一些领悟,所以特意提出来与大家分享。
唐宁:美国一些出版商曾评价《迷谷》“有些奇怪”,学界对它的“奇”也多有论述,似乎它已经是公认的难以归类。过去对于小说中虚构的“怪力乱神”,学者们倾向于将其表述为“想象力”,目前对《迷谷》的讨论似乎都是将其置于知青文学的类型框架内。事实上,在新书宣传期,无论是美国的出版方、独立书店,抑或是关注到《迷谷》的知名科幻文学播客等,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对小说的奇幻元素感兴趣,对此您怎么看?您认为它可被视作“奇幻小说”吗?是否可以说明具有“奇幻色彩”的中文小说在当下更容易受到海外读者青睐?
苏炜:这就要回到前面讲到的“独一份”的创作动机了。在写实的框架里写出超现实甚至反现实的意蕴,这正是《迷谷》的“迷”和“奇怪”之处吧。今天不少论者以“神幻”“奇幻”或“怪力乱神”名之,用我自己的表述,则不妨称《迷谷》为一部“世态奇情小说”。“世态”者,首先涉及的就是它的写实根基。《迷谷》的大背景是“文革”“知青上山下乡”,写实(历史的真实和细节的真实)是它的“刚需”,所以写作过程中我是紧抓住场景和细节的真实着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