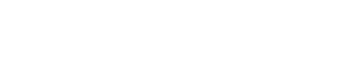前阵子,脱口秀演员小鹿去做美甲,听见两个年轻女店员聊天,其中一个讲:“指甲是女人的第二张脸。”另一个又讲:“我最近又听到说法,说女人除了第一张脸,哪里都是第二张脸。”
这其实是小鹿以前在台上讲过的段子。但她没吭声,也没被认出来。
相比长相,脱口秀演员的声音与文本可能更先被记住和认出。小鹿很少被人在公众场所认出,“主要我太素了”,平时不化妆,穿得休闲,有几次,她的声音先被认出来,而后才对上脸,“这是小鹿,说脱口秀那个”。
小鹿出生于1991年的云南,在成为一名脱口秀演员之前,她做了七年的法学生。毕业后,小鹿来到北京,开始接触线下脱口秀。直到2020年的《奇葩说第七季》,她以辩论选手的身份被更多人所知。
在北京初秋的一个雨天,我见到了小鹿。临近中午,原先约定的咖啡厅开始有点吵闹。本想更换一家,小鹿抵达后,见我已经点好一杯咖啡,觉得“不能浪费”,于是拜托店员拿了两个蒲垫到店外临街的窗台前。我们面朝漉湿的落叶和周一早上寥落的行人坐下。
9月,沉寂近一年的脱口秀重出江湖。单口喜剧竞演节目《喜剧之王单口季》里,小鹿穿一身白色婚纱上台,让观众印象深刻,“穿着它嫁人,也穿着它骂人”。
她讲了两个与自己的婚礼有关的段子,她“搞七搞八”,她的澳大利亚丈夫却“搞不清楚状况”。笑声雷动中,小鹿也笑了。
婚礼是在今年夏天举行的,这段感情已有七年,她告诉南风窗,她的本意并不是真的要抱怨婚姻。
脱口秀演员往往从切身经历里挖掘素材,现实里再微小的磕碰都可能在喜剧里撞出火花。小鹿讲关于化妆和年龄焦虑,讲妇科检查时的荒唐和羞耻感,讲现代人的电话恐惧症……笑声是对痛苦的软化处理,小鹿说:“不是所有负面情绪都能写成段子,但是段子几乎都来自负面情绪。”
喜剧是一种很有包裹性的创作。真实生活中的尴尬、愤怒和困顿,都可以被包裹进一个轻质的、幽默的外壳里。而好的脱口秀演员,往往擅长将日常精确化和陌生化,与受众达成一种连结,与世界构成一种良性的对抗。
在我们熟悉的脱口秀演员里,小鹿是看上去相对冷静的存在。可与她聊天,一下子能感受到她浑身散发的那股稳定的精气神。是如今流行的“松弛”也好,是大浪淘去后被阳光拂出的生命力也好,小鹿好笑,但更重要的是,她能给人带去真正的快乐与思考。
“喜剧是可以容忍的悲剧性”
去见小鹿的路上,我在雨后的胡同里偶遇了她的丈夫托马斯——前阵子那两段婚礼脱口秀的主人公。
三个月前,小鹿举办了两场婚礼。北京一场,老家云南一场。婚礼是她全程自己操办的,从试婚纱、婚鞋,准备伴手礼、邀请函……前前后后忙了差不多一年,随着婚期将至,小鹿忽然发现,大部分事情都是她自己搞定的。老家云南那场婚礼,混乱和文化碰撞被端到了台面上。
小鹿的澳大利亚婆婆与家人正襟危坐,云南老乡却忙着将饭菜打包。小鹿的爸爸原本还想让她在婚礼上表演5分钟脱口秀,“幸好没答应,不然婚都结不完”。
小鹿站在台上,铿锵地说,“我的婚姻可以失败,但我的婚礼不行”。
真是如此吗?不,恰好相反。
“虽然听起来好像我在表达不爽,但我们的底层是相爱,因为相爱才会走进婚姻。”
在举办婚礼之前,小鹿和丈夫谈了整整七年恋爱,“如果我要结婚,结婚对象只可能是他”。
小鹿站在台上,铿锵地说,“我的婚姻可以失败,但我的婚礼不行”。真是如此吗?不,恰好相反。“虽然听起来好像我在表达不爽,但我们的底层是相爱,因为相爱才会走进婚姻。”
托马斯是个很容易感到快乐和幸福的“普通上班族”,对中国社会的文化和习俗了解有限,在筹备过程中,小鹿感到自己操心和负担更多,结婚前夜,她崩溃了。烦躁之下,她拒绝与托马斯沟通。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托马斯发了一整晚的消息。小鹿回复一句,那边又即刻弹来回复,“这说明他一晚上没睡”。
那天早上,两人重新敞开心扉聊了很久,化妆前竟然还一起哭了一小时。前一晚,托马斯和伴郎团吵了起来。伴郎也都是外国人,“有的喝醉了,有的翻译错了词……他(托马斯)就像是拿着个狼牙棒在打狼一样,他也exhausted(精疲力竭)了”。
小鹿知道,“他尽力了”。丈夫再尽力,也只能做到这么多。婚礼让她心力交瘁,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她对自己的高要求和标准,她是一个容易“紧绷”的人。
在这段持续了七年多的爱情里,小鹿感受到明确的幸福,虽然也感受过明确的情绪,但它们是构成幸福真实性的必要元素。婚礼的“混乱”也是其中一部分。她接受它,面对它,然后调侃它,“但这是一种安全的感觉”。
其实负面情绪永远是喜剧创作的情感基底。“我觉得婚礼所包含的一些所谓悲剧性的地方,恰恰就是喜剧可以容忍的悲剧性。”就像小鹿小时候喜欢看的星爷的电影,长大后再看,她会看哭,笑着笑着,“一下子眼泪就下来了”。这是喜剧的本质一种。
婚礼是在今年“六一”儿童节举行的,“因为我觉得我俩都像两个小孩子走进婚姻”。亲密关系对小鹿而言具有吸引力的一面是:“你在外面需要做一个披荆斩棘的大人,但回到家里,两个人都会做回自己最初的样子,无知、可爱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