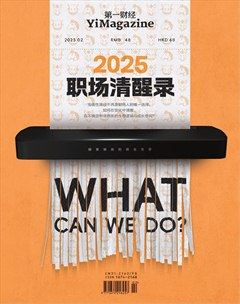2024年10月,秦皇岛鸟类博物馆。
“最早的观鸟记录,来自英国籍鸟类学家约翰·拉图胥(John DavidDigues La Touche)。他在1914年发表的《秦皇岛的春季鸟类迁徙》,是距今最早的有关秦皇岛湿地的鸟类调查报告。”
入口处的第一块展板,醒目地向访客回溯这里的鸟类观测历史。除了把拉图胥的国籍弄错之外,其他部分还算严谨,玻璃展柜里还摆放着他在“一战”后编写的《华东鸟类手册》。
拉图胥是一名爱尔兰籍海关官员,1882年他追随同是爱尔兰人的赫德,为秦皇岛海关效力。作为鸟类和动物专家的拉图胥,他的贡献持续至今。2014年,有研究者在上海南汇再次记录到北极鸥,而这种珍惜鸟类上一次的观测记录,就来自1908年的拉图胥。
“这些传教士、外国人没一个好东西,他们从中国偷走了茶叶!”两个中年人从我身边走过,行色匆匆中瞥了一眼展板,在我身后扔下一句狠话。
汽车从鸽子窝边上的马路上疾驰而过,阳光下婆娑的树林背后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湿地,时不时有一两只长焦镜头晃入眼帘。司机告诉我,一年一度的秋季观鸟季已经拉开了帷幕。100年过去,这片湿地上当年拉图胥孤寂的身影,已经被一群群拿着长枪短炮和望远镜的观鸟爱好者取代,这里已经成为著名的东亚观鸟圣地。
和几位艺术家朋友一起,我来到秦皇岛参加海碧台方栈艺术驻留。选择这里,除了这几年一直在进行的重走李希霍芬之路项目与此有关,还有我的“拉图胥情结”作祟的原因。
我并不是观鸟爱好者,第一次得知拉图胥先生,并非因为自然领域的知识,而是一次国外旅途中的邂逅。2016年,我有幸参加爱尔兰东北部多尼戈尔郡的一次国际媒体旅行团。为了让记者们对爱尔兰有一个深度了解,组织方给我们委派了一位非常出色的考古专家马丁先生全程陪同讲解。一来二去,我和这位马丁在路上有了交流。后来,他主动跟我这名团里唯一的中国人聊起他的家族先人过去曾在中国工作,直到退休回国。原来,他的外曾祖父就是这位拉图胥先生。
回国之后,马丁和我互通邮件。他给我发来这本鸟类手册的封面,我则让他继续帮我打捞一些这位先人在中国的家族轶事。不日,他发来回信:“再三询问,我妈妈对外祖父的记忆的确已经模糊,但对他从中国带回来的金刚鹦鹉却有着鲜活的回忆,因为它活得比他还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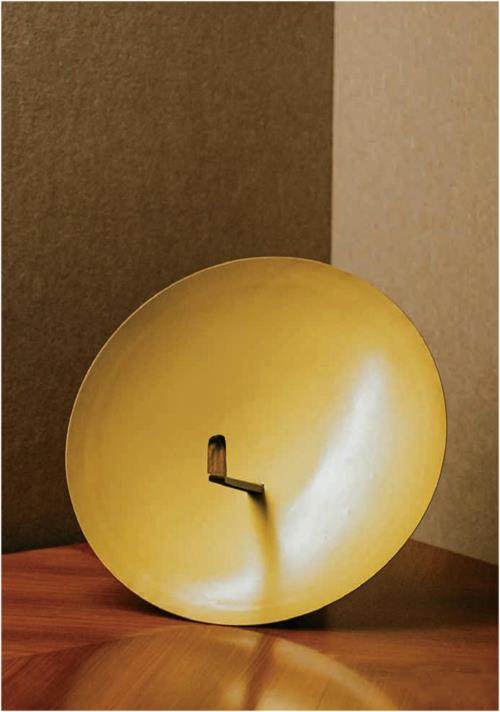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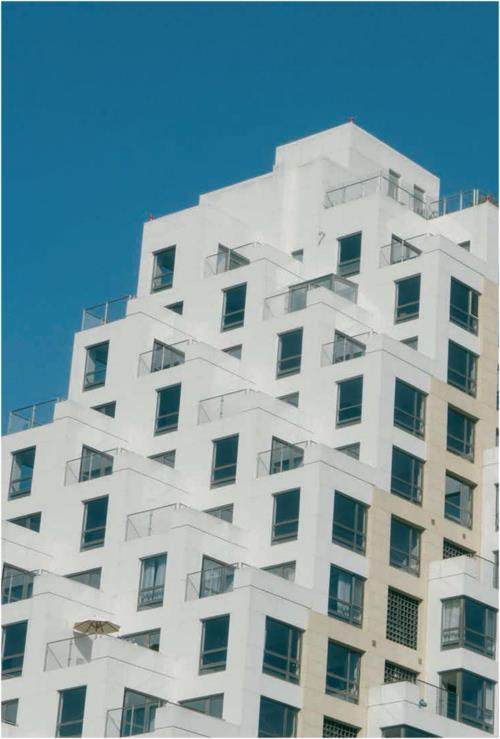
在《秦皇岛候鸟的春季迁徙》这篇报告里,拉图胥强调秦皇岛是一个very dry(非常干)的地方。这种气候特征,也是从柏林来的艺术家李亭葳认为秦皇岛和柏林最大的区别。
虽然同在北纬最适合栽种葡萄的区域,但这种气候依然是此地昌黎滨海葡萄酒产区和欧洲同纬度其他产区的一个重要区别。1905年的冬天,美国农业局派遣的调查员迈耶在昌黎为当地一个种植葡萄的农户在他的架子下留下了一张难得的照片。迈耶惊讶地发现,这里的葡萄藤必须要埋入土内才可以过冬。
这种埋土过冬的做法,直到今天还盛行。昌黎西场村,这个当年荷兰传教士文欣华最早带动当地人开始酿造葡萄酒的地方,今天已经改名为葡萄沟。小寒刚过,这里的冬天马上迎来一年最冷的季节。在一个树立着红色十字架的坡地上,我见到了看护教堂的焦如海的后人。据家人介绍,他们的太公是最早跟随文欣华信教的当地村民。据老人回忆,这里种植玫瑰香的历史有三百来年,但村民们一直不懂得用葡萄酿制葡萄酒。而今天,在修葺一新的村教堂里,当我问到玫瑰香葡萄酒的酿造历史时,他的曾孙女会第一时间把它和耶稣的血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