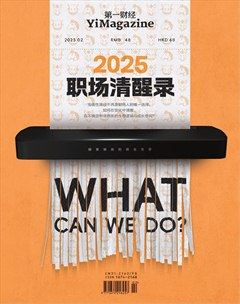Yi:YiMagazine
L:林垚
01
Yi:你曾经说过,“对男性而言困难的不是读多少女权主义理论,而是有没有做到。回头来看,之前没有做好。”当时发生了什么,让你产生这样的反思?
L:不仅是一件事情,回头去看整个人生,总会觉得我之前可能有什么做得还不够。你会发现很多人把女权主义理论说得很好,但在日常生活中反而还不如一个没读过多少书或者看起来很保守的人参与到家务、育儿的程度高。我爸爸初中都没有读完,但他会主动做家务。我上大学后去拜访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到了他们家发现都是师母在做饭,男老师就翘起二郎腿坐在沙发上看报纸,跟你讲大道理。我非常震惊,在家里居然可以有人颐指气使,这和我从小的成长经验是不一样的。
02
Yi:阅读《空谈》和你其他面向公众写作的文章,能感受到你有很鲜明的判断、观点,这和其他学者所写的面向公众的文章不太一样,为什么会选择这种写作风格?当你强调规范论述的重要性,不希望简化问题,与主流的观点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时,这种坚持有没有令你受到两边的攻击?
L: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曾经有一段时间读过很多社论、时评,那些时评写得很畅快,里面有很多排比、比喻,但是读完后你不会觉得他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很多时候这些社论是打马虎眼的,我上大学时就觉得很不满意。而这些时评慢慢衰败的原因,除了审查、阅读习惯的改变,很多时候也是因为作者的说理非常粗糙含混,不够细致,他们可能对具体的政治生活中的复杂面相、知识有结构性缺陷,很容易被人抓到把柄。所以如果真正要跟公众对话,我认为必须要把很多东西讲清楚,而不是为了追求畅快、追求篇幅上的简洁而牺牲掉这些部分。我觉得论证和思想的传播本身更重要。第二个问题,任何参与公共讨论的人都会在某些时候遭受来自不同方向的攻击。有些人会很洋洋自得地说,你看我被左边、右边的人攻击,可见我多么遗世而独立,可见我们的思想多么超脱于党派之类。但我觉得除非你真正站在了光谱的最极端,没有人比你更左或者更右,否则你肯定左边有人,右边也有人。所以要心态放平和,如果要参与公共讨论,尤其在网络时代,网络会让你的声音更容易传递到无数不认识的网民那里,所以做好心理预期,只重视那些有理有据、能够促进你思考的东西,无视某些比较无效的攻击、谩骂,做好自我的心态管理。
03
Yi:你的妻子在给《空谈》写的序里,提到阅读你的文章让她“卸去玫瑰色眼镜”,对民主的理解超越“聚众成一”式的宣言。你在之前的一篇文章里提到自己创建《选·美》这个播客节目的初衷,是代替之前中文舆论圈里流行的关于美国的浮光掠影、理念先行、想象代替事实的叙事。回过头来看,你觉得大家的观念究竟是在被什么影响?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能轻易地找到“同声相应者”,并且笃信自己是清醒的那一拨。声浪大的人占据了更多地盘,其他人也有吃有喝。“掰扯清楚”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吗?
L:掰扯清楚当然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从个人的角度说,参与公共讨论需要个人付出很多的事情。但参与公共讨论就是这样,如果觉得吃力不讨好,觉得累了,也可以退出。我也没有觉得自己一直100%投入在做这些事情,我自己也会有觉得疲劳、时间精力不够分配的时候。包括最近这几年,在写作上我其实就倦怠了,基本没有怎么写东西。当然,主要是因为时间、精力不够分配。但我也不觉得好像我自己退出了天就塌下来了。肯定会有其他愿意做这些事情的人继续参与。如果他们累了,可能有别人再顶上去,或者我缓过劲儿了,我再参与下去。
但这里面可能有一个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平困境。如果每个人都觉得吃力不讨好而不付出,那公共讨论的质量就会更加下滑,你生活在这个环境里就会更加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