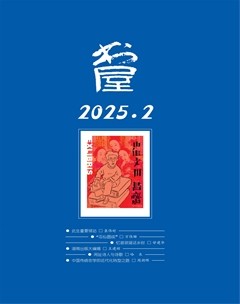一
1947年至1950年,我在广州南海中学念高中。
广州为什么会有个南海中学?
广州西边原属南海县,东边属番禺县。直到民国成立,各自的县政府才分别迁至佛山和新造镇,广州市政厅则迟至1921年才成立。番禺学宫曾挂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招牌,让它免遭破坏,而今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海学宫在米市路,现在仍存残迹,原地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的办公大楼高耸。
广州有个南海中学,加上在六榕寺附近的南海县衙门遗址和米市路学宫残迹,三点遥遥相望,留下南海县治曾在此间的印记。
惭愧,过去我很不了解母校!
谢虎成校长和江慧琼、曾哲老师收集翔实史料,编就《猗欤南海百粤光——广州市南海中学校史(1723—2018)》(吉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以下简称《校史》)。捧读以后,解开了我心中几个困惑已久的谜团,也增进了我对民国教育和政治复杂面貌的认识。
谜团之一,学校明明在西华路有个出入方便的校门,入学通知书和各种正式文书上为什么总是说校址在光复北路高第坊芦荻西巷?我入学时到光复北路,找到高第坊,走一段路才是芦荻西巷,走过斜斜的巷道,才看到那个古怪的校门:一个年代已久的灰黑色中式门,接着是由圆柱撑起的还有门厅的颇为威武的西式“二门”。弯弯曲曲的小巷寻门之路,实在难为了新生,特别是外地来的。大概是尊重久远的历史,舍不得把校址改写到西华路。
此外,同学中有人说这里原来是平南王尚可喜的“王府”。
读了《校史》才知道,这里原先是报资寺。平南王府(平南王府原址在今解放北路广东迎宾馆)不在这里,但的确与这位王爷有关。1650年,他率领清军围城八个半月,攻下广州,屠杀十二天,约十万广州府的平民百姓死于屠刀下,占当时广州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也许出于内心的恐惧和忏悔,后来他在广搜财货之余,扩建和新建了好些佛寺,有确切记载的是扩建大佛寺和新建报资寺。1673年至1681年的三藩之乱,他拥护朝廷,反对叛乱。其长子尚之信则反复无常,先叛后降,被赐死,尸骸埋在这里。尚可喜有三十七个儿子、三十二个女儿,从诗人、骚客的感叹中,可知此地曾经水波荡漾,芦荻护岸,榕荫蔽日,曲径飘香,真个清凉好去处,还有供人吊古挥泪、拈花澄心的禅堂。
戊戌维新前后,全国各地兴起办新式学堂的热潮,基本途径是书院改制,或没收庙宇办学。1898年7月,光绪皇帝发布上谕:“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着由地方官晓谕民间,一律改为学堂,以节糜费而隆教育。”戊戌政变后,慈禧垂帘听政,这条政策没被废除,特别是1905年废科举前后,此风继长增高。南海中学的诞生和成长,就是走光绪皇帝规划的书院改制和没收寺产的道路。
1904年,南海县将广州城里的西湖书院和院址在西樵山的三湖书院的资产合起来,年息二千元,在西湖书院原址办了一个简易师范科。1907年,改为南海中学堂,首任监督(校长)为朱世畴(勷寰)。稍后,经省提学使批准,广州城西的报资寺拨给南海县办学,经过几年拆建,南海中学堂于1910年迁到光复北路。
佛寺兴废,均在长官一念之间,财产权没有切实保障。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国民党组建的广州市政厅搜刮民财,以弥补军政费用,又一次把许多寺庙财产当作官产拍卖,闹得佛怒人怨。
旧门应是古刹原来的大门,西华路的“后门”是1928年才建的。
二
痴长八十七,回望一生,南海中学是我最重要的人生驿站。
在这里,我从一个说客家话、不满十六岁的腼腆少年,成长为共产党领导的秘密组织广州地下学联(青年团)成员和共产党员。从此,我的一生与共产党紧密相连,把争取自由、民主和国家富强作为不变的人生目标。在革故鼎新之际,我们奉命悄悄地成立应变小组,组织住校同学巡逻,保卫学校。南海中学1949年10月前加入地下学联的有曾乃众、袁伟时、莫景威、何乃钊四人。10月14日解放军入城后至年底,又吸收了高自强、苏嘉楷、曾乃博、扶展鹏、黄业标、冯永源等六人。1950年上半年,广州市大学、中学的共产党员分属两个支部。中山大学单独成立支部,其他学校合为一个支部,成员有:岭南大学卢永根、王屏山、蔡耘耕,广东文理学院陈积国,广东法商学院蔡贤书,广雅中学简乃强、陈国强、尹溢余,协和女中徐雪宾,知用中学黄炳忠,南海中学袁伟时。当时党员身份信息对外不公开。
在这里,我默默读了从图书馆借来、从汉民路(今北京路)大小书店中淘来、朋友们秘密传来的一大堆人文和社会科学著作,一期不漏读了《观察》和《世界知识》,也读了不少小说和诗歌。那时,从广州到家乡兴宁,路上很不平静,有家归不得。三年住在学校,尽享在教室一个人闭门读书的乐趣,遐思默想中孕育了仇视专制、追逐自由的观念,产生了向往刻骨铭心之爱的少年情思。后来,我在学术上做出些许成绩,无论知识积累还是治学方法,都归结于在这里奠立了初基。
2004年6月,我第一次回母校。那一天,《看世界》杂志总编辑周琪召集二十多位友人在人民北路一家餐馆聚会,悼念一周前逝世的著名杂文家、维护正义的勇敢斗士牧惠(林文山)先生(《红旗》杂志文教编辑室原主任),餐馆与我的母校近在咫尺。饭后我绕进西华路,校门口挂着广州市第十一中学的牌子,门卫听说是老校友来访,客气地让我进去。走遍全校,教学楼旁的参天大树和操场边上靠近芦荻西巷的两棵老榕树还在;新楼矗立,原来的宿舍、礼堂、教室、图书馆等老建筑已全无痕迹;镶在重建的半边亭上的一块石碑,居然不是原来的朱勷寰纪念碑……五十四年过去了,故人不在,故园也完全消逝!人非物非,黯然离去,心想大概缘尽于此了。
2005年,应邀到佛山市图书馆做报告,长期以来压在心底的对母校的思念再次萌动,我提出想顺便去市郊新建的佛山南海中学看看。图书馆一早派车到广州接我直奔西樵山,车子驶上大桥就看见巍峨的校舍。到达后,学校负责人热情地介绍情况,带领参观。一个设备先进、环境优美、管理严格、成绩斐然的新南海中学!高兴之余,想到老校现状,难免有点失落。
峰回路转。2006年,十一中复名广州市南海中学,老校复苏了。校庆日,同班同学相约回去看看。校史室展示百年历程,昔日校园和师长的照片嵌在墙上,勾起缕缕思绪。我为母校再生而欣慰!
从初创到1953年改为公办的广州市第十一中学,南海中学先后有七位校长,任职最长并把学校带至巅峰时期的是曾校长(1924—1938,1946—1953)。他教我们世界史,用英文教材,讲得很清晰,同学们也认真学。但他不苟言笑,与同学甚少交流。
根据诸如此类的片面印象,许多同学都觉得曾校长和事务主任罗楹存老师严肃古板。罗老师喜欢训人,同学们的乐事之一,是背后叫罗老师的绰号,学罗老师训人的腔调。
读了《校史》,我为自己的少不更事而脸红!
曾校长和罗老师都曾是激情澎湃的热血青年,爱国,追求自由、民主的热忱绝不落后于人。
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两千余人在租界游行,就日本纱厂镇压工人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之事抗议示威。英国巡捕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十三人,重伤数十人,逮捕一百五十余人。“五卅惨案”,震惊中外。
为支持上海同胞,广东人做了两件大事:
一是从6月19日开始,二十五万人开展省港大罢工,坚持了一年多。省港大罢工的主要领导者是苏兆征,他的秘书是共产党员罗楹存。
二是6月23日,十多万工人、商人、学生在东校场集会,会后游行到沙面(当时的英、法租界)对岸,投掷石头等物到租界泄愤。英、法士兵开枪,当场打死五十多人,其中一位是南中学生;一百七十多人受重伤,轻伤者不计其数。
6月23日,三十二岁的曾校长率领南海中学师生参加集会和大游行,在被迫撤退过程中,他的长衫被撕烂。
南中人维护正义的爱国之心一直在跳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第六天,曾校长召集全校师生开抗日大会,成立抗日委员会并自任会长。委员会组织三十个演讲队、募捐队在市区和各乡奔忙一个多月。其后,热情不减,继续用各种方式支援前线。南海中学支持抗日的活动居广州各校前列,与中山大学同为媒体最为关注的对象。
曾校长住在校内香泉楼,家则在清平路一栋三层小楼。曾校长住二楼;未婚儿女住在三楼,楼梯可以直达。他的十三个儿女,我认识七个,其中四人成了我的朋友。他的四公子乃众是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同班好友,同时也是我参加地下学联的介绍人和单线联系人。我对他家情况略知一二,他在广东文理学院物理系念书的二女鹜珠是地下党员,芷珠(执信女中学生)和乃众是地下学联成员(青年团员)。一中、二中、华侨中学、执信和南海中学好些地下学联成员都是他们发展的。后来一中、二中和侨中的成员交由我联系。他家还是共产党广州市工委的联络点。我们和二中、执信女中几个同学组建的秘密读书小组,有时就在他家三楼聚会。
那时,共产党给学联布置的任务是团结同学,保护学校,迎接解放。1949年9月,国民党军一个自称连长的人闯进学校,找到处理日常校务的郭尔悫老师,要求给他一间房,并让他的家属住进来。郭老师严词拒绝,而暗地里参加了纠察队的同学已围上来,保护郭老师以免受到伤害,那位连长只好灰溜溜跑掉了。
有件事我记得一清二楚:我在南中上学期间,校内没有国民党和“三青团”的活动。曾校长是广东文理学院历史系和外语系的教授、系主任,还兼任学院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和“三青团”干事长。完全由他作主的南海中学,却把国民党、“三青团”拒之门外。同时,学校的行政架构中居然没有训育处和训育主任,我也没有听过他和其他老师讲国民党的官话、套话。
这些举动的合理解释是,他在保护自己的学生,以免卷进当时的党派纷争。不同于对反动政府的欺压,他义愤填膺,全力抗争;也不同于对日本侵略者,他国仇家恨在心。1945年春,国民党军队大溃败,湖南、广西大部和广东北部(包括战时临时省会韶关)沦陷。当时,曾校长远在流亡粤西的广东文理学院,大女儿在去找他的路上,留在韶关来不及逃离的夫人和两位尚未成年的女儿被日寇强奸。国仇家恨,不共戴天!随后,内战炮火纷飞,国民党到处迫害共产党人,学校不能不考虑现实环境。如何应对,任何人都会踟蹰再三。他选择了政治中立,希望学生认真读书,尽快成才。
二十世纪上半叶,为数不少的教育家和士绅秉持这样的态度。教育救国,人才兴国,是他们念兹在兹的大事。
三
为什么要办私立南海中学?1922年,南海县政府要把学校迁到佛山,改为师范学校,并停发每年五千元的经费。旅港南海商人极力反对,毅然每年捐资九千至一万元,把学校改为私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南海中学的兴盛,离不开在香港的南海商人的鼎力支持。1922年,旅港南海商会在文告中说:“国家需人才,人才需学校,其说不易矣。比年来干戈兴,学校废,人才式微,国家胡赖?”先贤们正是秉持着这个信念办学的。
那么,他们要培养怎样的人才呢?看看1930年出版的《南海中学概览》中对培养目标的界定:“本校成立有年矣,训育问题,向来重视。而于训育方法,尤再三致意,务期适应社会之需求而又不戕贼个人之本性。一方面固保全吾国‘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美德,一方面发展‘自由’‘平等’‘博爱’‘独立’之精神。”“养成信真理与公理的态度,坐言起行之习惯。训练专门的与办事的才能,发展协作与领袖的能力。发展并坚定为公众服务,为公众谋利之兴趣和志愿。养成克己、信实、高义、勇敢、公平、同情、虔敬等习惯。”
回望历史,民国肇建,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他发表文章指出:“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
1929年,陈寅恪先生撰写的《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南海中学的领导者,虽然把1929年4月颁布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登在《南海中学概览》的封里,实际上却不顾有关规定,选择步武蔡元培、胡适、陈寅恪之教育理念,把“发展‘自由’‘平等’‘博爱’‘独立’之精神”“养成信真理与公理的态度”,作为培育学子的规范。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此远见卓识,真令我拍案叫绝,非常崇敬!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南海中学编创了校歌,师生传唱:“猗欤南海百粤光,衣冠气独昌。风节文章,亘古振遐荒,岿然我校继芬芳。”期许学子继承士大夫的风范和高风亮节,写出声情并茂的“文章”,为社会作出应有的奉献。
当时,国民党政府要求学校推行“训育”,上面派来的训育主任胡作非为,学校于是请他们回去,并争取到自行聘请适当人选的权力。学校还伸手向上面要经费,终于要到每月四百元(按当时物价,不算少了),拿到的钱用途之一乃是办《南中校刊》,刊登校内消息、游记、诗歌,统计学、钱币史等方面的学术论文。完全不见所谓“训育”文章。骨头不硬,没有风节,不敢这样做。
为了培育人才,南中锐意改革:实行学分制;数、理、化和世界史采用英语原版教材;要求根据现代心理学原理,对学生分类指导;与此同时,管理严,考试也严,主要科目两科不及格者,即使只差一分,也要留级。
学校鼓励成立各种研究会,让学生编校刊,规定“对于学生之活动,绝不加以干涉,以资自治之真精神,而锻炼各生运用民权之特殊能力”。自由讲学之风也吹到南中,讲学者包括张君劢。他是著名哲学家,燕京大学教授,《新路》杂志的创办人和主要撰稿人,一位勇敢批评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政治家。
培养自由、平等、独立之精神,不是徒托空言。
四
是不是抗战胜利后,南中就一蹶不振了呢?仔细想想也并非如此。
当时广州的中学分三大类。众人眼中广州最优秀的中学,非广雅中学、中山大学附中莫属,且两校难分伯仲,都是公办的。其他公办的市立一中、二中、三中、四中,省立执信女中,都属好学校。教会学校中,培正、培道、培英、真光、协和,以及岭南大学附中,都在水准线以上。对于这些学校,没有哪一所人们敢说一个“差”字。其他私立中学则良莠不齐,知用中学、南海中学是其中的佼佼者。
教育的本意是提高国民的素质。按此标准对照检查,南中于国于民没有亏欠。
南中文化基础课老师的水准很高。以1948年来说,任教的三十五位老师,其中有五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各大学任教授、副教授,而留在中学执教的很多都是非常杰出的教师。例如,郭尔悫老师是公认的广州中学数学教师“四大天王”之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我惊喜地看到,在广州最有名的艳芳照相馆的橱窗里挂着郭老师的大幅相片,注明是“广东省劳动模范”。其他如孔昭皋(国文)、李可通(英语)、黄云波(生物)等老师,无一不是同行中的出类拔萃者,其中,黄老师后来还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通货膨胀严重,公立学校教师叫苦连天;私立学校收学费、发工资都用港币,生活较为稳定,吸引了众多优秀老师在南中专心教学。南中没有教学不认真、教学效果很差的老师。默默坐在图书馆门口的管理员曾乃乐,并不起眼,“文革”时期辗转到了蕉岭县日用杂品公司工作。由于精通英、法、越三国语言,他被调至蕉岭中学教英语,后来成为蕉岭师范学校教师,负责全县英语教师培训;1982年更调至县教育局,负责全县英语教学研究,直至退休。这也足为南中教职工水平不低的佐证。
包括蔡元培在内的许多教育家都十分重视美育,一般学校却把它视为点缀。母校则把“陶冶审美、娱乐高尚、纯洁之性情”“增加欣赏或艺术的能力”摆在重要位置,践行了先进的教育理念。
谈点亲身的感受吧。
抗战胜利后,南中有四五百名学生,有叶柄森和陈丽峰两位美术老师。叶老师的课叫“劳作”,实际教我们雕塑。课程的前半部分先学素描;后半部分是“玩泥巴”,各自到文德路买胶泥回来,捏制大小物件。有美术天赋的同学则雕塑人头,制模做石膏像。确实是费劲的劳作!陈老师教国画,主要教工笔花鸟。班上李济荣的雕塑和刘敏中的国画都很出色。李济荣给自己塑了一个半身像,博得同学们一致赞扬。后来,他们远走高飞,与广州的同学失去联系,不知他们在美术领域是否有所成就。两位老师教的技能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但他们培育的美感和美的精神却让我终身受益。
陈老师上课,手抓两支工笔画的细画笔,一边画,一边叮嘱:要留白,要舒展大方,要有书卷气。这“三要”他每一堂课都讲,而且还示范怎样留白,如何才算舒展大方等,令我终生难忘。对其含义则囫囵吞枣,尤其对什么叫书卷气,我一直不太明白。几十年后,看别人的画作多了,特别是有一天看到某位名气很大的画家的一幅题为《万山红遍》的大作,居然满纸红艳,立即感到其失就是违反了陈老师所说的“三要”。不留白,没有留下思维自由飞翔的空间;笔下不见几千年来中国知识阶层引以为傲的刚劲风骨;没有悠然自得、舒展大方的气度。这不就是陈老师所说的书卷气缺失吗?绘画与做人,息息相关。陈老师的三点提示,意蕴很深。
每次南中同班同学聚会,我们都高歌曾嫩珠老师教的“Auld Lang Syne”(十八世纪诗人彭斯根据苏格兰古老民歌改编的名曲,电影《魂断蓝桥》主题曲《友谊地久天长》):
Should au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Should au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days of auld lang syne?
歌声久远,但永不消逝的友谊与艰辛、欢乐交织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曾老师的教学风格与众不同。别校音乐课教简谱,曾老师教五线谱,教的是世界著名民歌,课本用英文版的Famous Folk Songs 101。这些民歌感情真挚、曲调优美,随意哼吟,即令人舒适、上进。抗战期间,曾老师是马思聪团队的成员,新中国成立后是广州音乐学院教授。由音乐家教中学的音乐课,我们幸运如斯。曾老师以高雅的音乐和自身的高雅感染我们,即使像我这样五音不全的学生也深受其益。
说起音乐,顺便说说同窗中遭际坎坷的区庆照,他在街道工厂工作,终身未婚。记得在南中读书时,他多次邀请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同学到他家欣赏古典音乐,并认真讲解。我终生喜爱古典音乐,他是我最早的启蒙者。“文革”中,他珍藏的黑胶唱片被毁,之后竭力收罗,迄今伴随他度过孤独时光的依然是莫扎特、贝多芬。贫贱不能移,这不就是南中要我们传承的风节吗?
教我们公民课的潘老师是一位资深律师。这门课请律师来教,可谓别出心裁。从待人接物的礼仪,到现代社会的基本制度和运行规则,乃至如何开会,如何选举,公民有什么权利、义务,等等,他都讲得清清楚楚。
母校的美育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曾校长重视美育,真有远见卓识!而公民教育是更重要的素质教育。
南中收取学生,胸怀很宽。那时没有户籍制度,只要入学考试合格,不管来自哪里都可以入学。非本地的学生通常占百分之二十,有时高达百分之三四十,中国香港、澳门,甚至东南亚的家长慕名把子弟送来求学,并不罕见。1946年复校后,余风尚在,加上广州市民来自大江南北,更不计较学生的出处。来自香港的同班同学李济荣、家在西贡(胡志明市旧称)的初中生李琦,一直与我住在同一房间。
学校学习风气很浓。逃课、考试作弊、打架等恶习,在当年的南海中学几未见过。住在学校宿舍三年,我只见过一次同学吵架,在室友劝解下,口角也很快止息。
从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来的曾校长,终生不脱离教学,他既担任广东文理学院历史系、外语系教授和系主任,而且眼睛盯着世界教育先进水平,为办好南海中学,考虑周详,措施得力,不愧是一位杰出校长和教育家。
优秀教师与先进、严格的制度合力,培育出高素质的南中学生。
反抗侵略,反抗专制,南中人勇于献身。二十世纪中国英烈榜上,有一位在“六二三沙基惨案”中没有留下名字的南海中学学生,有在三十年代为左翼文艺牺牲的龚明烈士,还有在下乡宣传抗日途中倒在日寇枪弹下的许介烈士。
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年代,南中人也展现了自己的风范。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毕业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莫伯治为例。五十年代,莫先生受命建设广州北园酒家,他融合传统与现代建筑艺术,考虑地方特点,设计出独特的园林式酒家,并先后十多次到珠三角的旧建筑材料店收集“废料”,用在酒家的建筑上。莫先生化“废”为宝,设计、建造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精美建筑。酒家尚未建成时,就有人认为与潮流不合,提出要拆掉重建。他顶住压力,并在有识官员支持下,坚持按原方案建设。1958年,广州北园酒家被建筑大师梁思成教授誉为“广州最好的建筑”。这就是风节文章。
此后,他的“文章”越做越漂亮。广州泮溪酒家、南园酒家、白云山山庄旅舍、南越王墓展览馆、白天鹅宾馆……多少地标性建筑,都出自他的手笔。行内专家说他设计的建筑,“从传统和地方建筑艺术中吸取养分,演绎完全现代化的空间结构,为岭南新园林建筑树立了样板,影响持续达数十年”。到白天鹅宾馆,站在磅礴的“故乡水”面前,谁不感到这是一首扣人心弦的诗呢?
五
先行者筚路蓝缕的成果有目共睹,实至名归,南中在1937年被教育部检定为全国最优的九所中学之一。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校友的光辉如今或已泯没,犹待后人发掘。余生也晚,未能获睹。
管中窥豹,仅以再平凡不过的我们雷社同学来说,四十二位同窗中,至少有六位是在海内外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教授,其余同学也在不同岗位上有大小不一的成就(好些同学失去了联系,不了解他们的情况)。可以告慰母校的是,五十年后再相会,与会者有个共同点,都堂堂正正做人,没有一个在品德上被人诟病。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广东有个特别的印记:陈济棠掌管广东的时代(1929—1936),在老一辈广东人的记忆中,是令人难忘的。它与南中的辉煌在时间上重合,绝非偶然。胡汉民、陈济棠等广东人所促成的独特生态,给广东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带来更大空间。经济繁荣、海珠桥、中山纪念堂、粤汉铁路全线贯通、广州东郊一万二千多亩(当时全国最大)的中山大学新校园建设、中大的经费和设备超过了靠中央政府拨款的北京大学,如此等等,都是这个时期的成就。南海中学确立先进的教育理念,实行各种新举措,离不开扩大了的空间。
从一所中学看民国教育,政治与教育牵扯互动。空间稍大,则办得有声有色!洪水滔天,书生无力抵御激流,也当力求保持应有水准,为未来储备人才。“国家需人才,人才需学校……人才式微,国家胡赖”的呼喊扣人心扉,教育家无不期望年轻一代具备精英风范、报国才干。透过母校命途的跌宕起伏,我深感此类神圣愿望能否实现的关键是学校有无足够的活动空间。
对前贤的处境应有更多理解。
就以我很不满意的学生活动空间狭窄之事来说,细细想来,其实当时空间没有完全封死。
第一件事是我们班同学不少人喜爱读课外书,班会议决大家交钱买书,班主任谭福瑛老师和校方都很支持,立即拨给我们一个书柜。其中包括鲁迅著作的全部单行本,《观察》和《世界知识》杂志。我负责买书和管理图书。
另一件事是学校鼓励各班定期出壁报。我们班的壁报办得精彩纷呈,内容新鲜。有一期我安排同学将艾青写于1942年春的长诗《黎明的通知》全文抄下,放在最显眼的头条位置上,宣告“请叫醒一切的不幸者……说他们所等待的就要来了”,居然引得孔昭皋老师驻足观看。我估计孔老师和其他老师未必知道艾青是何许人也,也未必知道这首诗的真意是迎接快要到来的抗战胜利和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
在校内认真读书、写作,在老师眼皮底下活动,学校不吝支持,但害怕我们在校外活动闯祸。
再以我耿耿于怀的南中老校园被拆毁一事来说,关键因素应该是中学教育任务的改变。私立南中学生人数最多时没有超过八百,肩负的教育任务是精英教育。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原有校舍被拆毁,当时的紧迫任务是普及中学教育,校舍扩建势在必行。如果学校领导人和教育局的官员懂得百年文物的珍贵,拆迁比邻的民房或购地建新校园,当能两全其美。
历史没有后悔药。这不仅仅是南海中学的失误,“文革”结束后,一些文物建筑反遭摧毁,类似之事并不鲜见。1946年,南中复校所借用的南海学宫,后来只剩下残迹,那是始建于1293年的元代建筑!仅以十九世纪来说,科技奇才邹伯奇(1819—1869)和康有为等著名人物都曾在这里度过不少岁月。面对久远、辉煌的文化殿堂,某些肉食者毫无虔敬之心,竟然下令拆掉!
近年与谢虎成校长和南中的其他老师多次交谈,既感受到这个团队锐意进取的虎虎生气,也感受到客观条件下他们的诸多无奈。
遥想当年,郭尔悫老师讲解完一道方程式后,必然微笑着站在讲台前面说声“Q.E.D.”(证明完毕——这一问题已解决),然后开讲新内容。郭老师沿用古希腊数学家这一习惯用语,那么自然,流露出他上承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的学术气派。任重道远!1950—1953年,曾校长已无法照料学校,郭老师出任校务委员会主任主持大局,实际是私立南海中学最后一任校长。我深信,今日南中领导团队,也会解开一道又一道难题,说声“Q.E.D.”又翻开新的一页。
2019年,母校建校一百一十五周年,谢虎成校长最烦恼的事是,想办一个寄宿班,却没有地方建宿舍。五年过去,当接力棒交到赵秉乾书记、余英校长手上时,人们告诉我,一座大楼很快就要动工了,办寄宿班指日可待。
历史真的要翻开新的一页了!
人工智能时代来临,历史再度呼喊“国家需人才,人才需学校”!展望母校未来,一百三十周年、一百四十周年、一百五十周年……南海中学——无论是广州还是佛山,南海中学教育集团,一定会不负众望,必将交出新的辉煌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