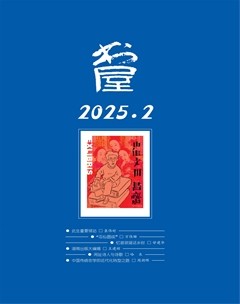2016年10月,我有幸被推荐参加了财新公益基金与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合作主办的“卓越记者驻校计划”项目(下称“驻校项目”),成为一名“驻校记者”,在中山大学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培训。我之所以被这个项目吸引,是因为袁伟时老师。
袁伟时老师自1957年起就在中山大学教书,时间比一个甲子还长。在我眼里,他是中山大学的“镇校之宝”,是我国乃至国际学界的著名历史学家。“袁伟时”三个字,俨然成了一记符号、一种象征、一部厚重的历史。能与袁伟时老师面对面交流,近距离聆听他的思想见解,并向他请益获答疑解惑,是何等难得,何等荣幸。
我决意与历史握一下手。
一
早在2010年,我与袁伟时老师就有过交集。那一年,袁老师作为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评委,来到深圳参加好书评选。其时,该项目的发起及主理人是胡洪侠(注:我先生,下称“大侠”)。
有了袁老师,评书会上更加严肃而热烈。他端坐一头,强调所谓好书,要有“三能”“二高”。“三能”指的是能提供新知识,能安慰心灵、激励上进,能帮助人们分辨是非、深入思考问题。“二高”是信息增量要大,要捍卫和推进人类文明。他力推江平的《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和齐邦媛的《巨流河》,这两本最终都入选了当年的“十大好书”。
那一年的好书评选倍受关注,不单评委阵容强大,还有最终的“十大”书单:《重新发现社会》《朝闻道集》《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苏联的心灵》……本本分量很足。
正是因为评委的努力,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成了书界一个风向标,照亮了很多好书,为读者提供了上佳的选择。同为评委的我忝列其中,并没有“与有荣焉”之感,而是深深惶恐。我知道,面对历史,我知道得太少,懂得太少,反思得也太少。
到中大,“驻校项目”还没开启,我就迫不及待地与袁老师联络。
2016年12月1日,我如约来到中大南校区康乐园旁袁老师住处。
一见面,袁老师说:“咱们先来个君子协定,聊天的时候录音,录音后整理出来的资料给我一份,因为有时候我也记不住当时说的是什么。”太好了,我本来还犯愁能不能录音呢。
袁老师又问:“你看过我的书吗?”我嗫嚅,随口报了几个书名,如《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路标与灵魂的拷问》,还有网上一些散落的文章,零零碎碎,不全面,说完脸颊发烫。
袁老师没有怪罪的意思。他特地指出2016年3月香港再版的一部书《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增订版)》,最能代表他的思想观点。“本书初版于1992年,经过三次增订,字数由二十七万增至四十二万,是迄今最完备的版本。”
袁老师看重的这部书,前身就是《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1992年由深圳的海天出版社率先出版。在这部著作中,袁老师把中国近代史看作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要是有人问,你这部书说的是什么?除了说声‘请看目录’,我会说:这是一部探寻中国现代化的障碍和历史经验的书,也是以史料为根据说真话、说自己的话的书。”
多牛呵,“请看目录”成了后来大家多处引用的话,代表了一种骨气、傲气、不肯退缩的硬气。
可是,经济学出身的袁老师,为何转向历史,并在退休之后火力十足地写出多部思辨性历史著作?这是我最关心的。
“我是1931年出生的,当时‘九一八事变’刚发生几个月,我们一懂事,就是全面抗日战争,打仗,整个少年时期都是在抗日战争中度过的,所以特别希望国家强大。”“1949年念高中的时候,我就读过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还有范文澜的书,他们的文章对我的人生观影响很大,所以我1949年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秘密组织。”“我于1950年加入共产党,是广州解放后第一批加入的。1950年考大学时,我认为民主自由、国家独立都有了,现在要进行国家经济建设了,所以高中毕业后,就考了中山大学经济系,想参加国家经济建设。”袁老师娓娓道来。
从小就有阅读经验的袁伟时,对历史很感兴趣,开始追溯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