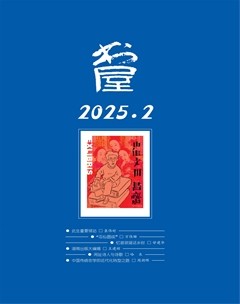2024年是劳承万先生的鲐背之年,也是先生从事教学科研七十周年。于我而言,这是一件非常重要和需要礼敬的事情。第一次和先生见面,是1992年在全国农展馆附近召开的美学会上,这成为我的人生和学术研究的重要转折点。在1993年至1997年间,我在先生主持的湛江师院中文系工作并执弟子礼,沐浴春风,聆听教诲,奠定了从事学术研究的根基。离开先生以后,我们交流密切,从书信到微信,延续至今。有一次和自己的学生聊天,曾说我们是真正的“名门正派”:国学源自刘梦溪先生,因为我是梦溪先生的大弟子;西学则源自劳承万先生,他是康德专家韦卓民先生的弟子。除了未能免以门第自高之俗,这也包含了一点微妙的愿望,即尽管自己跟随两位先生都学得不好,又转移了领域,但还是希望年轻人能接上这一高贵和纯粹的“学统”并发扬光大。两位先生尽管学术领域相去较远,但均为有道行、有风骨、能为青白眼的高士。相对而言,对偏居南海一隅的劳先生,我会更多一些牵挂之情。除了当年的知遇之恩,他的哲学美学研究也成为我最重要的学术启蒙和理论来源,不管是最初的美学研究,还是后来的城市研究。
先生的学术研究和贡献,一般被后学划分为三大领域:一是以《审美中介论》《审美的文化选择》《康德美学论》等为代表的哲学-美学研究;二是以《诗性智慧》《中国古代美学(乐学)形态论》和《中国诗学道器论》为代表的中国美学-诗学研究;三是以《中西文化交汇中近百年之理论难题》《中国文化之特质》《根系学术形态论》为代表的“哲学美学-中国古学”研究。其中,我个人学习且受惠最多的是哲学-美学研究。中国美学-诗学研究虽与我所从事的中国诗性文化研究有关,但由于他最看重的是牟宗三先生,而我曾提出要把牟氏的“以儒家改造康德”变为“援康德补孔孟”,所以与先生的共同语言并不算多。
关于先生的哲学美学对我的影响,曾有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二十年前,先生在推介我的《苦难美学》时写道:“一个穷孩子,向仙人求食,仙人的手指指向那里,那里便有吃不完的东西。最后仙人问穷孩子:‘满足了么,你还要什么东西?’这穷孩子说:‘我要你的手指头。’刘士林有点像这个穷孩子,他要的是康德的‘手指头’(先验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