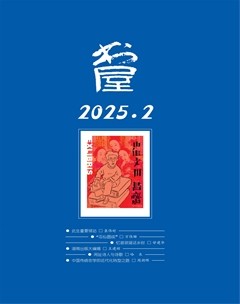艾青坐在对面长沙发上,前额宽阔的硕大脑袋懒洋洋地仰靠着椅背,目光投向天花板,他旁边挨坐着诗人徐刚。
我隔着茶几,恭恭敬敬端坐在旁边的单人椅上,开始采访:“艾青同志,我从初中时就喜欢您的诗……”艾青立马打断,拖长了声调:“都——这么说,都——这么说。”我不计较大诗人的不耐烦,自顾自表白,说自己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怎样在农场的水车旁读他的诗,读聂鲁达和希克梅特的诗,并且背诵了希克梅特一首完整的四行诗:
亲爱的,不,这不是空谈:
我像一颗子弹似的穿过被俘的岁月,
就任凭在这途程中,我得了病吧,
我还是那颗心,还是那颗头颅。
艾青似乎被枪弹击中了,一下从沙发靠背上抬起了头,移了移身子,用亲切的声调对我说:“你读了不少书。来,坐这边来。”一面示意徐刚腾出座位让给我。
大诗人的话匣子一下打开了,滔滔不绝地告诉我,聂鲁达、希克梅特都是他的好朋友。1957年,他到机场迎接他们,可他们离去时未见艾青去送行,他们敏感地察觉到这位中国同行倒霉了……
可今天,此刻,历尽苦难的艾青,与我这个同样历尽苦难的读者促膝长谈,凑巧我念出了“还是那颗心,还是那颗头颅”这几句,岂非这位大诗人怀着他不变的诗心重见天日、重返诗坛的象征?
为何会蓦然记起这件我早已淡忘了的发生在1982年夏天的陈年往事?是因为昨夜整理书柜偶然发现破旧笔记本上的一段摘录:“土耳其政府有意迎回希克梅特遗骨。”——2017年1月15日是纳齐姆·希克梅特(Nazim Hikment)诞生一百一十五周年。《土耳其每日新闻》报道,土耳其司法部长贝基尔·博兹达当天在议会发表讲话,赞扬希克梅特是“土耳其养育的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并表示将从莫斯科迎回他的遗骨以回葬的方式给予他荣耀。希克梅特被比作洛尔迦、阿拉贡、马雅可夫斯基和聂鲁达,在土耳其现代诗歌史上具有无可争议的地位,云云。
访问艾青的细节虽已淡忘,但关于希克梅特我记忆犹新,他与聂鲁达、瓦普察洛夫的书一直立在我的书架上。
希克梅特,当年,几乎是与多年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聂鲁达一起闯入我年轻的心的。他们一下子挤占了普希金、雪莱、海涅、施企巴乔夫等在我心中的地位。
但说来抱歉,我对希克梅特的了解,仅限于一本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希克梅特诗选》和我随手摘录于各种报刊的零星诗行,加上附于诗集后面萧三的一篇关于希克梅特的介绍——这是1951年11月17日,萧三在布拉格由世界和平理事会等举行的授给希克梅特“国际和平奖”典礼上的讲话。
多年来,我反复阅读希克梅特、聂鲁达、瓦普察洛夫,觉得他们有颇多相似之处。这种“相似”不仅限于他们三位,而包含了二十世纪全球有良知的知识者的共同命运:或为反抗强权制度与野蛮侵略,或为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或为让百姓能在自由、民主、公平、法治中安居乐业而奋勇战斗,甚至不惜牺牲生命。
希克梅特、聂鲁达都让我一见倾心。聂鲁达抓住我的是他那海涛般的狂野、浪漫、豪放。富有音乐性强烈节奏的诗行,似瀑布倾泻下来,激荡着,让人无法平静。而希克梅特的风格迥异。他的诗句,点射的枪弹似的,短促,有力,哒、哒哒、哒哒哒,一枪一个洞眼。比如:“十五处伤口在我的胸前,/十五把刀子,/十五个人的死。/但是我的心更有力量!/十五把刀子插在我胸间,/十五把刀子强制我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