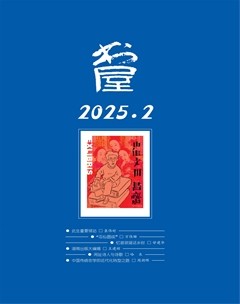一
大航海时代以降,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将商业贸易网络延伸到包括东亚在内的世界各地,与此同时,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加深。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明清时期,随着包括农学在内的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不断传入,中国传统农学和西方农学开始相遇、碰撞,中国传统农学逐渐走上近代化转型之路。
明末,西方近代农学开始零星传入中国,成书于1639年的明代农学巨著《农政全书》,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西学东渐影响之下的一大农学成果。意味深长的是,作者徐光启(1562—1633)不但是皈依基督教的学者型官员,也是西方科学最早进入中国的推行者之一。徐光启与耶稣教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作为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广为人知。而徐光启本人着力最著,平生最引以为傲的学习引进西方科技的成绩则是在农学上。《农政全书》中专设两卷《泰西水法》,介绍当时欧洲先进的水利技术,同时,徐光启也在上海松江地区和天津等地进行农学实验。代表时代前沿的农学著作采用西方科学试验方法研究农业生产技术,已经带有实证主义性质,开启了中国农学近代化转型的序幕,但某种意义上也显示以经验农学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农学走向式微。
而反观西方,在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学界逐步建立了科学体制,开始形成近代科学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基本态势。所谓的科学“体制化”,概而言之就是国家层面对某个学科提供配套支持系统。最根本的,一是由国家设立专门机构专司其职,负责对某个学科的研究、教育、推广、指导和管理工作;二是建立科研、教育、学术机构,由国家财政支持并接受国家行政管理。就中国而言,在漫长的帝制时代,科举制就是这样一个承担了文化、教育、政治和社会等多项功能的基本建制(Institution)。
诚然,自晚明至康乾时期,上至皇帝、高官,下至一般士人、书商,都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西方的科学与技术,甚至在明清之际中国也涌现出不少杰出的科学人物,也有一批不同凡响的科学著作问世,比如农学领域的《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等。不过他们对于西方科学技术的接受并没有触及当时的国家学术教育体制:一方面,在以儒家经义为核心的国家文教体制下,科学技术被视为旁门支流,科学思维与科学精神并没有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只是停留在个人兴趣的层面。即便是像徐光启这样位于时代前沿的科学家,创造性地使用“格物穷理”的概念来阐述西方农学,试图将西方科学纳入儒学系统,也并没有摆脱将科学活动附属于道统的窠臼。另一方面,正因为外来科技的接受在明清之际是个人层面的行为,故而缺乏相应的促进其发展壮大的制度层面的支撑。
明清易代之后,为加强统治,清朝继续加强闭关锁国,至乾嘉两朝,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传入的路径基本中断,晚明徐光启们开启的以农学为代表的中国科技又重新回到原来的发展轨道。1687年,牛顿提出的“力学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随着时代的发展运用在农业技术上,农业生产由传统的人力、畜力向机械动力发展,新型农具和机械得以广泛使用,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极大地改变了农业生产的面貌。十九世纪中叶,欧洲著名生物学家孟德尔通过作物杂交实验发现了生物遗传定律,从而使生物育种发生划时代变化。同时期清朝的农学家还在使用汇集了历代传统农学技术的官修农书《授时通考》指导农业生产——中国与西方在农业科技领域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
二
中国近代农学是引进的,而不是从传统农学中自然发展而来的。1840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惊醒了晚清帝国的盛世迷梦,中国社会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艰难历程。先是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的学习,如早期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运动。经历种种失败之后,再转向纵深的文化思想层面的学习,遂有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农学也在经历近百年的求索之后,逐步开始了近代化转型。
与率先引进的军事科技、数学、天文学、物理、化学和特定的工业技术等相比,西方现代农业技术传入的时间稍迟。在经历一段时间富国强兵的艰辛探索后,国家依旧没有改变积贫积弱的面貌,这促使精英集团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从更深层次反思强国之路,把目光投向作为传统基础产业的农业。被誉为近代第一位“睁眼看世界”的晚清思想家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记录了西洋“农器便利,不用耒耜,灌水皆以机关,有如骤雨”的先进生产方式。其后,王韬、郑观应、陈炽等晚清经济思想家也纷纷提出引进西方先进农业科学技术,以夯实富国强兵之根基的主张。1860年,清政府设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1875年,格致书室创办于上海。这期间,翻译西书的数量大增,共出各种西书五百多种,其中农学方面的书籍包括花之安译的《西国农政说》、李提摩太翻译的《农学新法》和《意大利蚕书》,另有英美农书八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