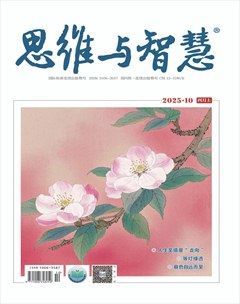一件皮棉袄
豫北农村老家有一件皮棉袄,父亲每年都拿出来晾晒,然后小心翼翼地折叠整齐,放在一个盛衣服的大木箱底层。那是母亲留下的唯一遗物。
出生在贫寒之家的母亲半个多世纪之前嫁给父亲。老家位于中原的大粮仓,加上国家救济,当时吃饭基本可以保证,但穿衣很困难。
从我记事起,母亲几乎终日为穿衣发愁,终日在田里劳作,累得全身浮肿。一到冬闲,她就摆起纺花车、织布机,终日纺花、织布,“吱吱啾啾”的纺车声和“咣咣当当”的织布声不绝于耳。年底,再染成各种颜色,为全家人做好过年的新衣服。到天热了,把棉花掏出来,改做单衣。但她自己一直是穿旧衣服,过年就洗得干净点。那时很少买成衣,我印象中,母亲就没穿过新衣服。
20世纪90年代初,我到南方读大学,母亲送我到县城,当时生活好多了,母亲为我特地买了一件衬衣,那么热的夏天,非要买长袖的,说是过段时间冷了也能穿。
几年后我结婚了,第一次春节回老家,妻子特地花2000多元为母亲买了一件当年很时髦的深色皮棉袄。一见皮棉袄,母亲怔住了,一个劲儿絮叨只在电视上见过人穿。一听价格,更是心疼:“你们工资就几百元,买这么贵的衣服,还怎么生活呀。”心疼归心疼,但母亲很“自豪”,穿上对着镜子前照后照,带着儿媳妇各家走访,逢人就炫耀:“这是儿媳妇专门买给我的,2000多呢。

登录后获取阅读权限
去登录
本文刊登于《思维与智慧·上半月》2025年4期
龙源期刊网正版版权
更多文章来自

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