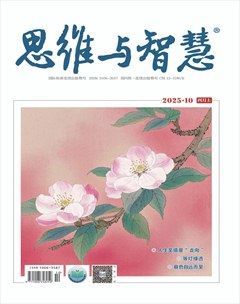暮色自远而至
黄昏古寺,偶读陈春成《竹峰寺》,尤其喜欢那段关于黄昏的感喟。
“有一种消沉的力量,一种广大的消沉,在黄昏时来。在那个时刻,事物的意义在飘散。在一点一点黑下来的天空中,什么都显得无关紧要……如果你在山野中,在暮色四合时凝望过一棵树,足够长久地凝望一棵树,直到你和它一并消融在黑暗中,成为夜的一部分——这种体验,经过多次,你就会无可挽回地成为一个古怪的人……就只适合日复一日地坐在野地里发呆,在黄昏和夜晚的缝隙中一次又一次地消融。”
消沉不是悲观,通透并非放弃。没有在黄昏时分独坐过的人,不足以语此。
喜欢黄昏,喜欢暮色四合的时刻。我曾经在黄昏凝视过门前的苦楝树一点点被暮色吞没,凝视过我的曾祖母在暮色四合时走向往生,凝视过老屋最幽秘的鼠穴被暮色堵住,但我并未成为一个古怪的人,就像元和四年某月某日黄昏的柳宗元一样。那一天,柳宗元坐于西山之上,四望“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不觉时移,“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暮色如水,如静默的潮,自远方掩卷而来。人如礁石,端坐不避,凝视着暮色的临近,上涨,淹没。感受着最后一丝光亮被吞噬,被熄灭,被消融,体验失去的恐慌、释然和解脱,定义“人”的概念——名、利、责任等等,会在黄昏消释,而作为“人”本身的“心”,却会在那个时刻凝聚成一个光点,在海一般的汪洋人间载浮载沉。

登录后获取阅读权限
去登录
本文刊登于《思维与智慧·上半月》2025年4期
龙源期刊网正版版权
更多文章来自

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