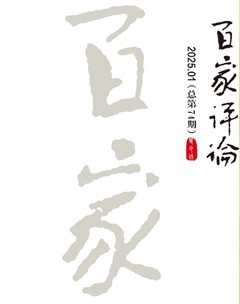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散文现场依然保持相当热度,涌现出不少有一定影响力和能见度的作品,但散文创作在艺术上的“革新”确乎乏善可陈。之所以如此,散文理论与批评的失语是重要原因。原创理论的匮乏与“先导”功能的缺失成为当下散文艺术发展中的瓶颈。从研究视野和话语空间来看,当下散文研究中理论抽象能力有待提升。从批评视角与路径来看,散文批评中动态多元思维有待强化。从批评对象与主体建构来看,对批评文本及批评家本身的关注,是散文批评获得自省以及由此改良批评生态的必要途径。
关键词:文体边界 理论贫困 批评方法论
我国古代文学历来以“诗文”为正宗,无数散文经典彪炳史册,素有“散文大国”之称。随着梁启超“小说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因“君子弗为”而历来备受冷落的小说被提到“文学之最上乘”的位置,其文体地位在晚清实现了戏剧性翻身。相比之下,被视为文学之正宗的“文章”至五四已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从文学发展史来看,“散文”虽然不能说就此一蹶不振了,却无疑成为寻求边缘突围的弱势文体。五四时期,鲁迅和周作人分别从魏晋文章和晚明小品中寻找写作资源,在改造探索中使“散文”在“随感”和“言志”两种文体创新中焕然一新。自此,“散文”的文体功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并铸就了20世纪30年代“小品文”a的辉煌。然而,这种回光返照式的繁荣景象,并不意味着散文轻易就摆脱了弱势文体的局面。直到新时期乃至新世纪,“小说”的绝对强势地位依然未能动摇,以致如今我们提到“文学”,潜意识里实在言说“小说”。只要谈起散文,往往给人以相对冷门的感觉,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当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散文热”极大推动了其文体地位的提升,这也是事实。但无论是从市场份额还是从创作实绩来看,散文在文类中的地位和受重视程度都远不及小说和诗歌。有学者称,散文已沦为一种“次要文类”,抑或“残留文类”。b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原因很多,但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本文主要从散文本体论出发,结合散文理论研究与批评的生态及其问题,阐释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互动对话的价值与意义,在此基础上探讨散文批评方法论及其可能性。
一、问题的提出
在几千年漫长的文学史上,作为中心文类的“散文”地位显赫,但很长一段时间,其文体界限似乎并不明晰。这种背景下,五四文学革命于散文而言有两大影响值得注意:一是历来被视为中心文体的“文章”走下神坛,意味着其唱独角戏的时代从此终结。二是散文的文体界限从混沌走向清晰,从与“韵文”相对的“文章”中分离出来。杂感、随笔、小品等新品种因此进入文学史谱系之中。当然,散文与诗歌、小说、戏剧“四分天下”之说,还是始于周作人的理论阐发。散文作为“抒情”和“叙事”的两大功能定位使它从大一统的“文以载道”的“定义”中独立出来,成为审美的现代性文体。即便如此,五四文坛对散文的审美独立性的认识显得并不那么自信。朱自清在《背影》序言中提到,散文“不能算作纯艺术品,与诗、小说、戏剧,有高下之分”,散文家的不自信,说到底,恐怕还是缘于缺少现代散文理论的支持以及文体边界尚未最终划定。
关于“文体”的认定,金人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七《文辨》中有言:“或问文章有体乎?曰:无。又问无体乎?曰:有。然则果何如?曰:定体则无,大体则有。”c于前者而言,鉴于不同文体之间边界模糊的情况,文体界说确有必要,但又常常使人陷入“误区”。人们常说:某某把小说写得太像小说了,或曰:某某把诗歌写得太像诗歌了。这其实并非褒奖之辞,而是隐含着批评的意思,意思是说,文体意识太强容易把自己的写作限定在固化的“定义域”中,有时候是作茧自缚,很可能会破坏文类“兼容”的艺术感觉。而“大体则有”所指的是,文体的边际是存在的,必须体认各种文类的大致特征、形态和规范。这是常态意义上的界说。然而无论中外,文学往往是在不断打破常态的过程中向前发展演变的。不难看出,王若虚对“文体”的辨析是颇有见地的,蕴含了历史的眼光和辩证的思维。就小说与散文而言,一个重于“虚构”,一个偏于“纪实”。这是大致上的区分,也是必要的界定。然而两者贯通的情况古已有之。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评论指出,作者在写作中打破文体界限,吸收“史迁之法”和“左氏之文”。而现代作家废名小说《竹林的故事》作为散文化叙事的范例,在文学史谱系中往往被视为文体创新的标本。这种“跨界型”写作常常让史家的文体归类陷入尴尬境地。鲁迅的《一件小事》《故乡》《社戏》等小说就经常被当作散文来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甚至被编入“散文”或“小说”两种不同文体的文集里。然而,从审美探索的角度来说,文体互动未尝不可,它不但可以激发创作潜能,也是散文创作趋优发展的重要动力。
基于文体之间互动频繁的基本事实,笔者以为,以历史的眼光和动态的视野去梳理分析“文体”的概念,可能会更切合实际一些。从文学艺术演变线索来看,小说、诗歌、戏剧与散文之间的文体互动是文学变革发生的重要动力。之所以这样说,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文学传统中“以不文为文”“以不诗为诗”革故鼎新之道,二是中外文学叙事模式的异同造成的“刺激”和“启迪”d。比如,当代散文中杨朔的“诗化散文”,当代小说中也有何立伟“绝句式小说”,汪曾祺的“散文化小说”就更不用说了。文体之间的互动与对话成为文学审美嬗变的生长点,是散文研究尤其是本体论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层面。当然,这种互动与对话也是有限度的。“跨界”写作并不都是有效的审美实践。尽管对于散文的“虚构”成分占比多少合适,我们很难加以量化,但是理论上必然存在一个黄金分割点,越过这个“点”,散文写作很可能会陷入被质疑的困境。
循此脉络,着眼于“文体学”观察散文艺术的当代演变,不难找出文体流变背后潜藏的内在规律。20世纪散文发展史上出现三次创作高潮:一是20世纪20-30年代品种多元的散文创作;二是60年代前后的“诗化”小说浪潮;三是新时期尤其90年代以来的散文创作。远的不说,就近30年来散文创作而言,“文化散文”“学者散文”“小女子散文”“白领散文”“乡土散文”“行走散文”“新散文”“在场主义散文”“新媒体散文”等创作现象引人注目。从命名不难看出,散文一直在文体探索中发展,不断向新时代文学高地发起冲击,寻求突围的可能性。这种探索中,每种创作路向的出场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彰显了自身的审美立足点,显示出某种超越性的诉求。然而,无论是“文化散文”创作潮流,还是后来的“新散文”实验性写作,其局限也都一眼可见。以“新生代”散文集《上升》来看,部分作品回避现实,“游戏典故”,醉心于主体隐匿后的“零度抒情”,更有甚者,像玩积木那样制造叙述和语言的迷宫e。说实话,这种“新散文”的倡导者在理论主张上过于偏激,如过度追求形式、全盘否定论等,还不惜走向理论的反面。f这似乎违背了“先锋”的本义,它是一种有愧于读者的写作,一种略显悖论化的写作。同时,由于在“文化散文”概念理解上的偏差,也在无形中降低了写作的难度。图书市场中大量所谓“大文化散文”泛滥成灾,出现“知识崇拜”(王兆胜语)倾向。笔者认为,主要问题在于创作主体的生命体验和心理经验被缩减到最低程度,即使有一星半点的个人感想,也往往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宏大历史讲述中。“知识性”有余而“艺术性”不足的问题普遍存在。当然,有了这样或那样的探索及其不足,散文领域始终保持着一定热度,甚至显示出与五四文学相媲美的氛围、生机与活力。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严肃文学被迅速边缘化,文学刊物面临生存危机。这种背景下,散文思潮多样展开,此起彼伏。散文界呈现出一派热闹的文化景象。陈剑辉将此一时期散文思潮归为四大类:通俗闲适散文、文化散文、新散文、在场主义散文。每种散文思潮的出现都与某一阶段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氛围有关。比如,通俗化闲适散文就能体现经济转型期社会文化心理需求的创作类型。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形式实验难以适应价值多元时代的精神需求,取而代之的是追求通俗易懂、符合大众期待的闲适散文。当然,精英主义文学的追随者并没有在商业化语境下全面失语,而是提出“文化散文”或“大散文”口号,与闲适派散文以及稍后的“新散文”构成多元并存的创作格局。总的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散文现场依然保持相当的热度,也涌现出不少有一定影响力和能见度的作品,但就文体的变革来说,与诗歌、小说、戏剧相比,散文是这几十年来所有文类中“最无所作为的”,“散文面临着艺术上的停顿,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辛酸现实”。g相对于其他文体,当代散文在艺术“革新”上,确乎乏善可陈。然而,散文创作之所以出现如此情状,笔者以为,散文理论与批评的失语恐怕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五四散文所创造的艺术高峰,就是在与散文理论建设互相成就的运转中实现的。这一点无疑值得重提和探讨。
二、理论贫困及其“先导”功能的缺席
散文在五四时期从“文章”统称中独立出来,走出长期以来文体暧昧混沌的状态。这一过程是在理论与创作的良性互动中完成的,并形成了多元散文美学竞相发展的格局。进入当代后,散文理论与批评显然落后于创作实践,未能承担起对创作实际的先导功能。理论与创作之间关系的非正常化,与散文文体边际的模糊有很大关系。朱自清对“散文”的界定就曾表示困惑,“因为(散文)实在太复杂,凭你怎么说,总难免顾此失彼,不实不尽”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