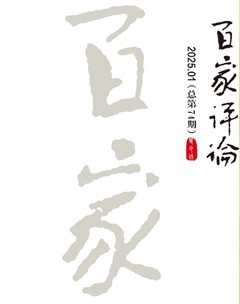内容提要:有人认为,历史小说如果过于强调历史写实,会影响作者创作手段、技巧的提炼运用,不同程度地牺牲文学的创造之美、文采之美、艺术之美。张鸿福的创作实践证明:历史小说完全可以在事实与真实、再现与表现兼顾的情况下,构建文史并秀的文学世界。他主动担起了历史小说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双重任务,他的历史小说在文学史学两方面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钩沉史海,借古喻今,主体性写实、少量虚构和大胆想象,使得小说有了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有据可考的可信度,文学史学相互成就,相映成趣,很好地满足了读者的历史文学鉴赏需求,很大程度弥补了读者历史学养的粗疏和不足。张鸿福的历史小说始终活跃着一种力量,诚恳地、真实地、厚道地讲述历史,心无旁骛对读者们进行文学滋养、文化引导和史学辅导。
主题词:张鸿福 历史小说 文学 史学价值
一
英国思想家科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指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是历史学家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科林伍德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历史小说创作,历史小说作家解决了历史学家叙事中思想与情怀、纪实与文采难以兼顾的困惑和困境,清晰明了地复原、重构历史的“本来面目”,以丰富的历史图景、生动的生活面貌、鲜活的人物故事、严谨的逻辑思维,让枯燥沉闷的历史变得绘声绘色意趣盎然,成为读者回望历史、壮阔胸襟、激荡心灵的案头读本。
从青年阅读的角度来看,优秀的历史小说,确实给他们带来了真实快乐的阅读体验和哲学思考。读书可以明智,读史可以鉴今,通过阅读满足读者的意趣情志和历史联想。历史小说独特的文学魅力和艺术审美恰到好处地照顾到每一个读者的个体情绪、精神愿望以及思维方式,从不同层面提升了读者通读历史、鉴古知今、顾盼未来的勇气,这是历史学家们难以做到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小说作家受“新历史主义”创作思想影响至深,“新历史主义”认为所有的历史书写并不能真正地还原历史,如果不能为读者提供可信的历史、文化资讯,不能准确塑造历史人物,片面地追求文学效应,忽视历史小说的信史成分,这样的历史小说未必有真正的文学意义。
“历史本身是不是文学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写历史必须要有文学的才华。”a自古“文史”一家,以文叙史是历史小说作家的优势,文学的张力之美和史学的朴素之美在小说家的心灵里合而为一,文学的创造力和史学的客观性很容易产生强大的引力,吸引历史小说作家废寝忘食笔耕历史,吸引读者在小说家创造的历史图景中本能地思考并与现实链接,让历史在现实中产生共鸣。一位优秀的历史小说作家,必定也是一位学养深厚的历史学家,没有严肃的历史学观,没有严谨科学、守正创新的创作态度,很难写出经典的历史小说。
近十年,历史小说作家张鸿福进入了旺盛的创作周期,一系列反映近代人物的历史小说磅礴而出,他的历史小说突破了“新历史主义”文学创作的局限,在“守正创新”上不遗余力,客观地、准确地、严谨地推导小说的史学价值,让枯燥的历史叙事焕发出崭新的文学意义,他一贯坚持历史写实主义创作,不放弃任何历史线索的探究和追溯,沿着历史的“草蛇灰线”小心求证,最大可能还原历史真相,他的历史小说逐渐固化成型,成为一种新的历史小说创作范式。张鸿福的历史小说很容易让读者深信不疑地进入他所勾画的历史情境中,有读者认为,读张鸿福的历史小说,获得的不是肤浅的情感体验和历史认知,而是在每一个历史事件的起因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感同身受,仿佛真实地参与了那段历史。
中国近代史是离读者最近的一片历史图景,也是最为壮丽、喧哗、斑斓、跌宕的人间镜像,对于今天的中国,最有比对、殷鉴意义。“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启了中国近代变革图强、艰苦备尝的探索之路,今天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是在此基础上一次规模空前的励精图治,前一次“变局”是极其被动的,是以虚弱的姿态,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探头探脑的无奈之举,而后一次“变局”则是中国以强大的力量和勇气,主动嵌入、自觉引导人们完成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世界性塑造。
张鸿福之所以选取这一段历史作为创作园地负重躬耕,应当说他受到了时代的激励,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和近代有极其相似的一面,更加需要我们保持足够的怵惕和清醒。他是一位有着强烈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的小说家,他认为他有责任来担当这一使命。张鸿福的近代人物系列历史小说,以其近乎逼真的历史背景、文明冲突、人物命运的书写,系统、真实、全面地把这一段历史呈现出来,宏大而瑰丽,像一面镜子放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近距离端详远去了的历史遗容,触摸一代王朝的日渐式微以至最终陨落,以此对历史先贤人物致敬,以此对读者精神、文化洗礼。张鸿福认为,对历史的反思,就是对未来烛照,对现实的觉悟,才是对历史最好的纪念。
正像科林伍德说的那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张鸿福近代历史小说是否是一部“思想史”,需要时间和读者做出判断。对中国近代史以文学的形式来表现,很多历史小说作家做了积极尝试,涌现出一批艺术造诣深厚、影响深远的历史小说作家,不可否认,他们对于近代史的思考和传播,对历史小说的艺术创新有很大的建树和贡献,但他们交给读者的往往是片段式的,是某一段历史的背影和侧面,读者从他们的小说中感受到的是以文学形态构建起来的历史框架,从来没有像张鸿福这样沉醉其中,以细腻的笔触、冷峻的思想,严谨的构思、独到的见解,让沉闷的近代史变得生机勃勃,从来没有像他这样固执的、忘我的、夜以继日在历史深处沉浮俯仰披沙拣金,以5部15卷600万字近代人物系列历史小说去讲述一段历史。
十余年来,张鸿福一直深耕近代这片丰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在史海里潜水,在史料中耕耘,在创作中反复推敲、酝酿、思考,如何用良知、学问、技巧和情怀对这段历史作深刻的解读,于是,他沉静了下来,辗转反侧,把心底波澜笔下乾坤变成优秀的历史小说。《左宗棠》《袁世凯》《林则徐》《李鸿章》《大清王朝1860》b以及《红顶商人盛宣怀》c等一系列历史小说联袂而来,丰盈地、完整地构成了近代历史版图。张鸿福的历史小说在文学上大胆探索、不断创新,在史料上潜心研究、反复考较、存真去伪、认真引用,因此,他的历史小说既“推心置腹”又“言之有据”,具有很高的文学、史学、美学价值。
二
历史小说作家不像现实主义作家那样具有高度的创作自主性,创作空间受到历史事件的约束和后人历史认知、历史评价的双重挤兑,越是接近历史的真实,留给作者创作空间就越狭小。历史小说作家在真实与虚构、技巧与情怀之间的取舍平衡,决定了小说的文学艺术性和史学价值。单纯以文学为目的的历史小说,不管作者的文学技巧如何高超,不管小说怎样好看耐读,都不足以成为经典的历史小说,相反,过分强调小说的史学成分,忽视了文学造诣带来的美学意义和阅读享受,同样不被读者认可。
张鸿福的近代历史小说很好地兼顾了文学的美学意义和史学价值,在严谨中求放达,在孤闷中出新意,时代的戏剧性、文化冲突、生活情境在他的小说中波澜起伏枝叶鲜活,他的历史小说具有普遍的历史写实、象征意义,一帧帧绮丽清晰的历史镜像,一幅幅生动鲜活的生活画卷,一幕幕委婉曲折的人物故事交相辉映,文学带来的艺术享受,真实可信的史学表现,所产生的历史回响发人深省。短短几年时间里,《左宗棠》已出3版印刷7次,《李鸿章》已出2版并多次印刷,《袁世凯》也在再版之中,可见他的历史小说受到读者怎样踊跃地欢迎。
近代是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最为高涨的一个时期,对内对外斗争荣辱并存的不朽往事在他的笔下历历在目。不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小说家,他们的眼中的近代史是混沌迷茫的,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向来莫衷一是,左宗棠、林则徐、袁世凯、李鸿章、盛宣怀,近百年来在国人心中形成了一致的成见,这为小说创作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张鸿福的历史小说半文半史,不偏不倚,一半用史学的立场,廓清近代以来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根脉由来,探寻深藏在每一个历史事件背后的真实原因,一半用文学的立场,复盘时代镜像、历史场景、人物风采和文化精神,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在文明冲突面前,左宗棠、李鸿章、林则徐、袁世凯、盛宣怀等一批卓越的思想家、政治家、实业家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人性之光,才会得以最准确的描摹和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