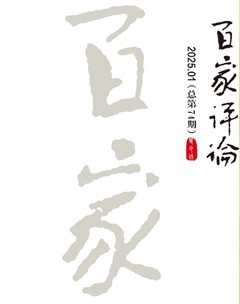内容提要:本文围绕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展开重读分析。该小说以土地所有权变迁为驱动,通过多个闭环交叠,展现农村人性、情欲和道德的交错重构,瓦解了传统农民概念,呈现“离土农民”的情感断裂与精神困窘。作者采用冷静客观的回望式叙述,以“宁家家运”起兴,塑造“腻味”“宁可玉”等时代符号,展现历史沧桑与人文伦理扭曲。小说还借费左氏、银子等女性命运,暗喻土地易权带来的传统道德蜕化异变,完成土地与女人的隐喻通途。作品延续现实主义深化道路,书写农民人格变化与重建,对当下仍具深刻意义。
关键词:赵德发 《缱绻与决绝》 土地 农民 女性命运
2024年10月,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带着一些遗忘的钝感和重读的敏锐,我与这本书一并重新切入了初冬,书中无数细节在沉冥中又重新闪动着耀眼的光芒。
一、在几个闭环的交叠中完成对主题的建构
这部小说被张丽军先生称为“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黄钟大吕’”,堪称一段浓缩版的中国近代土地史。此刻的阅读更像是一种深沉的回望——向着那个曾经大地沉寂而人声喧嚣的年代。故事一直由土地所有权的发展变化为驱动,通过人与土地之间关系的记述,上演了错综复杂的农村的人性、情欲和道德的交错与重构。
《孟子.滕文公上》说:“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农民与土地互为依托关系,两者之间有着牢固的联结。本部小说的主人公“大脚”就是这样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对土地有着“宗教般的生命皈依”。他给自己的地都起了名:“镰刀把”“算盘子”“破蓑衣”……从这些名字上可见,这是一种基于现实关系之上的、田园牧歌式的精神寄托;不仅如此,他对土地的挚爱还表现为不断地开疆拓土,先是在自家山场开出两亩圆环地。因为开地,老婆绣绣把第一个孩子都累掉了。如果我们站在俯视的角度,就可以看到在这块圆环地里,“走一年甚至永远走下去也走不到头”,大脚是这块土地的王者,它承载着他将土地永世不竭、千秋万代传承下去的畅想和希望。因此,“土地”构成了大脚现实与精神的双重维系,同时也勾勒出本部小说中“缱绻”的情感轮廓。
后来,大脚又买了6亩地,加上分家时的18亩,合并起来成为一个“中农”。但这些土地却“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随着“高级合作社”的到来,土地被征收了上去。在这之前,大脚祖辈一直生活在封建土地所有制这样一个封闭系统里,这让他一时难以“醒悟”,并走进一个新的土地时代。为了生计,绣绣只好替他出工,在原先属于父亲宁学祥的土地里,绣绣回忆起那些为争夺土地而死去的人、逝去的事……当下轻易的交出土地——这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与沉重的、血淋淋的过往交叉再现,被诠释出一种关于土地的虚无与荒诞。直至发展到后来的“分田单干”,土地在颠沛流离的大脚身上完成了一次完整的闭环。
与大脚命运并行的“铁头”,则是土地易权的另一种显现。大脚娶了绣绣后,又到费左氏家多“揽”了十三亩地。这些地原是铁头租种的,无地可种的他只能去“工夫市”打零工。在那里,他被发展成县农会的重要成员。于是,有觉醒意识的铁头带着几十个锄地户去了地主家,争取到“永佃权”……后来,在“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分户单干”“两田制”几个阶段,铁头和他的儿子封合作一直作为土地政策的“代言人”,领着村民与土地分分合合,从土地政策的演变上完成了另一种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