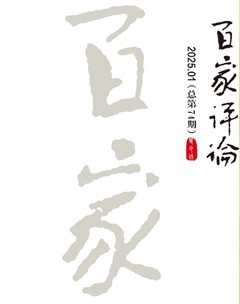内容提要:王安忆的情感叙事紧密关联社会变革与时代潮流,呈现出多维书写向度。“三恋一岗”系列突破集体话语的桎梏,聚焦女性情感解放与主体觉醒;《米尼》《我爱比尔》等作品转向市场化浪潮中情感异化的书写,批判工具理性对人性的侵蚀;《桃之夭夭》《启蒙时代》等作品探索情感教育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以此强调情感应回归人性本质,在物质化与符号化的时代中重构精神自足。通过情感叙事与社会结构的复杂互动,王安忆的创作为当代文学提供了观照人性本质与存在价值的多元视角,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与哲学深度。
关键词:主体建构 情感异化 理想人格
王安忆创作的情感叙事始终与其对中国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思考紧密相连。从20世纪80年代的“三恋”、《岗上的世纪》,到90年代的《米尼》《妙妙》《我爱比尔》《香港的情与爱》,再到21世纪初的《桃之夭夭》《启蒙时代》等作品,王安忆以文学创作为时代镜像,通过剖析个体在宏观历史进程中的情感挣扎和生命律动,深入探讨情感与社会结构、时代命题的复杂交织,极大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情感叙事的表达范式与内涵,为理解社会与个体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多元视角。
一、情感觉醒与主体建构
在“十七年文学”中,个人情感表达被长期抑制,取而代之的是投身革命事业的集体话语。直至改革开放,“人”和“人道主义”重新走入知识界的视野,私人感情才得以在文学作品中重现。人道主义的复兴标志着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中心从阶级斗争、政治宣传转向对“人”的关注。写“人”,就要写人的命运、人的情感。但在改革初期,人们更关注“伤痕”与“反思”的共名表达,对女性的情感需求仍避而不谈。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和宗璞的《心祭》中精神之爱与身体之欲的割裂,恰为女性情感需求仍受压抑和隐匿的辅证。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安忆的“三恋一岗”充分展现女性在追求爱情过程中迸发的鲜活、真实的强大生命本能,书写女性主体意识的苏醒,成为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思潮的先声。
《荒山之恋》中大提琴手成长于一座“高大阴森”“黑洞洞”的老宅,祖父常以检阅、杖打儿媳等手段来强调家族等级,彰显自身权力,形成对子孙、儿媳的禁制。“文化不仅压制了人的社会生存,还压制了人的生物生存;不仅压制了人的一般方面,还压制了人的本能结构。”a这种家族权威对个体的凝视挤占了自主人格的发展空间,使个人成为自身需求的严格管控者,任何需求的满足都被视为不可饶恕的罪行。即使在饥荒的极端情境下,大提琴手也无法直面自身对食物的基本渴望,将“饥饿”视为一种道德上的罪恶。这种成长经历在压抑需求的同时也禁锢了生命原力的发展。大提琴手从心底不相信自己具有独立面对外界的能力,生活的各个方面皆依赖于妻子的强力推动和扶助,他实际上并没有完成从儿童到成年的蜕变,其“逃避的梦想”b指向自我的实现,与金谷巷女孩的结合成为大提琴手实现自我的契机。作为“进取型的女子”,金谷巷女孩一生都在无意识地追寻女性主体的自我确认。她惯于通过挑逗异性反复确认自己的女性魅力,“知道他在她不远的后面,知道他在看她,也知道他有点喜欢她,心里便十分快活”c。女孩从小从母亲处习得驾驭男性的技巧,自我认知陷入了高度性欲化的身体注视渴望。她在这种挑逗游戏中获得自我确认和成就感,一再俘获男性构成了她的自我实现及与外部世界的对话。
王安忆持续思考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可能性契机。《锦绣谷之恋》中全篇没有情欲场景的直接描写,但女编辑的情感苏醒及随之而来的主体建构构成了小说叙事的核心和线索。她对男作家的依恋和向往,伴随着对自我女性身份的反复确认。和男作家相遇后,女编辑想象着他的凝视,并为此鼓舞。这种男性凝视赋予了她的行为以意义,激发了她对“新的理想”d的追求。在确认男作家对她的关注后,作者细致地描写了女编辑照镜子的行为。起初她以内观的视角审视自己,与镜中的自己对话。然而,当她细察自己各种角度时,视角转变为想象中的男作家的视角,将自己的身体视为客体。在这种视角的转换中,女作家从情感主体转变为男作家的欲望投射对象。随后他们之间的互动,伴随着女编辑对这种男性视线的持续探询。当男作家拥吻她后,她“重新意识到了,自己是个女人,她重新获得了性别”e。在临别前的无聊时光中,女编辑忽然对这段经历和自己的性别产生了怀疑,这时男作家轻按她的头,“她浑身的血液都冲到了头顶,她以她浑身的血液来体验,来回应这只手,她以她浑身的血液亲吻着他的手心”f。这种澎湃的激情,与其说是两人真正的相恋,不如说是女编辑对自己女性主体和身体魅力再次确认而引起的兴奋。作家不无尖锐地指出,“一个女人的知觉是由男人的注意来促进和加强的”g。1949年新中国建立初期亟需集中全部劳动力加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反映在文学叙事上,爱情的表达被转换为投身社会建设的集体热情,女性尤其是获得主流认可的英雄女性形象存在明显的“男性化”倾向,性别特征遭到隐匿,潜藏其间的既有集体对个体的遮蔽,也有传统性别观对女性的围攻和打压。父权秩序的文化叙事多从男性视角展开,女性形象常以男性凝视下的客体呈现,长期他者化指认使女性难以建立主体性认同,其自我想象往往从男性情欲化视角出发,《锦绣谷之恋》中女编辑对自我性别的反复追认从而形成了时代思潮中女性性别意识觉醒的叙事模拟。
深入考辨,对女性主体性建构的探究本质亦是对普遍人性的探究,“人都是社会的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我想寻求的是拥有不同生存方式的男性和女性在获得这种无功无用的人性的快乐时,他们是怎么对待的。”h《小城之恋》中男孩和女孩身体的畸形阻隔了他们自我价值的实现。在剧团中,他们既得不到尊重,也无法在集体中取得位置,只能将所有的生命激情、能量都投入到情欲中去。环境对他们生命激情的禁锢,反而助长了个体的本能反抗。《岗上的世纪》中李小琴对杨绪国的“勾引”“献身”和“控告”都有着明确的功利目的。然而当李小琴招工失败控告杨绪国后,俩人分别遭到了伦理和法制的“围堵”,他们却在这种围堵之中,在岗上的小屋中度过了几天几夜,招工、控告及家庭责任等都被悬置,只剩下情欲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