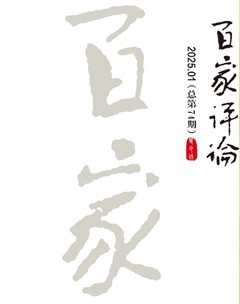内容摘要:魏思孝的文学创作历程中存在从前期的“小镇忧郁青年”叙事向“乡村三部曲”之后专注乡土题材的明显转折点。转折不意味着断裂,打破自我主体性边界并与他者的外部世界产生联结的意图通过女性形象的接续和对情感题材的转型得以实现。同时,作家通过操弄叙事视角使得笔下的叙述者不断获得合法性进阶,最终以“我”的第一人称叙述语言重新回到乡土语境之中。
关键词:精神焦虑 不连贯状态 叙述视角 第一人称
魏思孝的小说创作自“乡村三部曲”问世以来,一直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辛留村”的乡土世界,乡土文学的坐标系上已经赫然写上了魏思孝的名字。严家炎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认为乡土文学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出现的第一个小说流派,它的前身是作为五四文学之先声的问题小说a。正如柄谷行人所论“风景”是在现代被重新发现的装置,“乡土”也是五四青年经历“觉醒—出走—再归来”这一启蒙路线后被重新发现的题材。因此,乡土文学的形成与发展中埋藏着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丰富线索,每一次思想的解放和思潮的更迭,都让同时代的作家带着新的眼光重新书写和讲述乡村。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凡是涉及乡土风情人物的小说创作,都可归为乡土文学的范畴。然而魏思孝并不是一个乍出即以书写乡土立身的作家,当我们理所当然地将魏思孝放入乡土文学的范畴之前,有必要探究这位年轻的作家走向乡土题材、确立自身文学话语的路径。
一、“小镇忧郁青年”的精神焦虑
2017年,何平发表在《花城》的《除了“伤心故事”,年轻作家如何想象故乡?》一文将魏思孝归为“小镇青年作家”,那时候的魏思孝刚刚出版《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何平如此指明小镇青年写作的未来发展方向:“在他们写作的年轻时代,可能要向他的前辈和兄长辈的苏童、朱文、阿乙、曹寇学习如何书写‘故乡事’,而不只是‘伤心故事’”b,很显然,小镇青年写作在很多研究者看来仍是一种文学创作的幼稚形态,夹杂着跟风起哄的热情和无病呻吟的腔调。当魏思孝后期转向看上去更扎实和厚重的乡土写作之后,他在“小镇忧郁青年”时期的作品被研究者直接归为一种不成熟、尚未成型的写作见习期的产物。魏思孝在后来和李黎的访谈中说道“小说上,我骨子里其实是南京人,在阅读匮乏的学徒期,我看了‘他们文学网’的所有网刊,后又按图索骥阅读了韩东、顾前、朱文,以及后续更年轻的你、曹寇、李樯、赵志明、朱庆和。十多年过去,以‘他们’为根基的南京作家群,不论是从知趣还是文本上,都在影响着我。我身上留下文学的烙印。不谈国外,仅在国内,抛开其余零星几个喜好的作家,这就是我的文学母本。”c此时“乡村三部曲”已经问世,由小镇青年到乡土人民群众的转型已经发生,但魏思孝仍然强调这一群奉后现代趣味、后启蒙理念为创作圭臬的文学群体对自己的深刻影响,因此“小镇忧郁青年”写作是魏思孝艺术生命中一个重要时期,不是可被简单划为先声或者草创期。
2010年魏思孝出版第一本小说《不明物》,这部长篇小说处女作鲜有研究者或评论家提及或关注。“我”(刘骨)大学毕业后在出版社做编辑,偶然通过朋友张除非认识了住在市委大院的李雅婷,在和李雅婷的接触中,“我”心生歹念,想对她进行侵犯未果,匆匆逃离,被小区保安抓捕拷打并没收了身份证件,逃亡到一个外地小县城投奔网络上认识的诗友马学病。在这样近乎流浪的生活中,“我”和马学病还有杨文菌仿佛掉落在社会的缝隙,他们在陌生的城市里游走,没有工作也没有目标,每天行为动机只有谈论女人、追逐女人。他们渴望性爱也渴望自由,他们的内心并不安宁,不知道自己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他们在追逐女性的过程中,常有一种复杂的不合时宜的情绪,引向感情中注定落败的宿命。一方面,他们对女性的渴求中带有强烈的攻击意图和掠夺倾向,另一方面,这种与女性不恰当、难以把握分寸的交往中肆意涌动的情欲,又常常因警察、安保人员等社会权力机构的暴力介入而遭受强制打断。马学病和公关小姐李汝南的相互纠缠,“我”和余小烟的同居生活,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公关小姐李汝南因自己的工作身份受到马学病的调侃备受侮辱,选择自杀;“我”甚至因和方小烟亲热时警察突然上门调查而受到了惊吓,从此患上了阳痿。
巴塔耶在《情色论》中认为,人类渴望和追求连贯,然而每个人自身都是一个完整的封闭结构,连贯并非生命的常态,这就注定了我们难以和其他个体生命发生真正的联结。性和死亡都是人类从不连贯状态进入连贯状态的途径。“情色一开始引人注目的是:一个精打细算、封闭的现状被满盈洋溢的脱序所动摇……动物的脱序可以自由自在地沉溺于无边的暴力中。在断裂完成、狂暴洪潮平息后,孤独再度闭锁在不连贯的生命中。唯一能改变动物个别不连贯的是死亡。”d在魏思孝的“小镇忧郁青年”叙事中,性的意图与行为总是被外界秩序和权力代表强制打断,这意味着主体不断地陷入非连贯的、与他者无联结的孤立状态。KTV公关小姐李汝南、住在市委大院的李雅琪,不仅是小镇青年眼中情色符号,更是钱和权力的化身,这些刚从大学毕业走上社会的乡镇青年出于原始性欲的驱动接近她们,但在他们从小耳濡目染的已被商品经济重新组织过的文化符号环境中,性总是作为一种消费资源存在,因而成了附着于钱和权力实体之上的符号,这些“小镇忧郁青年”无法分辨自己关于与他人联结的渴求和对性作为经济资源的侵占欲之间的区别。他们追求个体之间联结的原始欲望无意之间触犯的却是现实社会的经济逻辑从而受到了暴力的制度压迫。每一次与异性的交往,最后向他们显露的不仅是感情的失败,本质是他们无法获得参与社会资源分配和交换之资格的贫瘠底色。
对于女性和性的想象,是魏思孝小镇青年叙事中的一个显在症结。《不明物》之后,2013年到2014年间,魏思孝先后在豆瓣上发表了《恭喜发财》《该男子已被刑拘》《近食勿分》等五部体制精短的电子短篇小说集。后来这些短篇小说被选编入《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出版。这几部网络短篇小说作品中延续了《不明物》中的小镇无产漫游者的形象,除此之外,作家加入了关于杀戮和死亡的情节。比如《恭喜发财》书中的人物在世俗的失败和人际关系的孤立中而逐渐生长出畸形、变态的心理和行为方式,“我”扪心自问,“什么时候会成熟起来。早几年前我认为自己有能力在社会中干点什么,即便做不到妻妾成群号令一方再不济小富则安还是没问题的,我不着急,信心满满。几年就这么过去了,具体也说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或许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此,什么也没发生。我们像是角落里的老鼠,白天闭门不出天黑也只是四处张望,怎么也说不明白。”这里的“我”的精神处境便是上文所说完全脱离社会关系的、与他者无法形成边界交融的封闭状态,由此催生对于自我肉身的想象,试图通过这种肉体性的暴露实现对自身主体性的结构从而打破边界。这不禁让人想起20世纪90年代一度形成潮流的身体写作,离经叛道的形式之下性的意义被解构,控制走向了被控制,极致的联结导致更绝对的断裂和孤立,最后指向自我死亡和自我虐杀的想象。
研究者大多将“乡村三部曲”看作魏思孝的转型之作,认为在“乡村三部曲”中,魏思孝的关注对象断崖式地转向了乡村社会,小镇青年的忧郁苦闷、无病呻吟仿佛一夜之间化为乌有。然而在《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和“乡村三部曲”之间,2016年发表在豆瓣的由五部短篇小说组成的电子短篇小说集《农村妇女探究》中藏有魏思孝创作转向的重要线索。小说集名字中的“探究“二字表达了作家探究欲和探究方式的转型甚于关注对象的转移。第一篇《杨美容》里,叙述者这样形容这部小说的诞生缘起:“在我恬不知耻的一再追问下,才发现自己对生活了三十年的乡村,是如此缺乏了解。我感到羞愧,并不为乡村里频繁的通奸之事件,而为自己对乡村的一贯的冷漠态度。”e可见,叙述者的兴趣和好奇点和之前的小镇忧郁青年一脉相承——女人的“失节”和其背后的伦理失序。
这部网络电子出版读物在网络上的阅读量不大,但第一次显示了作者对农村地域群体的关注,女性是他从小镇忧郁青年的个人小世界转向乡村世界的结合点,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转向并不是所谓走出个人的空虚的精神世界,而是从忧郁的情绪转向了这种情绪发生的语境,假如这种情绪来自某种匮乏和贫瘠,那么是哪里失衡了?叙述者在“探究”的过程中,并没有对这些农村妇女做出负面的评价,相反,客观的叙事呈现的是妇女“失节”的必然性,这里的失节并不仅指的是通奸行为,还有传统乡土伦理秩序的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