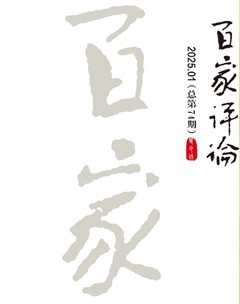内容提要:在百年中国朗诵诗的历史演变进程中,诗人与诗评家对“何谓朗诵诗”这一重要议题展开了持久而深入的论辩,力图辨清“朗诵诗”与“非朗诵诗”的文体差异,识别“朗诵诗”的诗体特质,营造有利于“朗诵诗”成长的舆论氛围。重审中国朗诵诗诗体理念的递嬗,可以让人们更好地勘察与思忖中国朗诵诗的来路、进路与新路。
关键词:百年中国 朗诵诗 诗体特质 理念递嬗
“五四”以降中国朗诵诗走过了百年的风雨历程,为中国新诗的有声传播提供了丰富的文本资源。20世纪中国朗诵诗在时代风云际会与流转中,适时感应时代的召唤,以独特的声音景观激发诗歌的生命活力。朗诵诗作为“一种听的诗”与“新诗中的新诗”a,在成长过程中既要确立独特文体的样式,不断提高朗诵文本的识别度,又要调整与优化可听化诗歌文本的功能与价值,让朗诵诗永葆充足的生命元气,为此当代朗诵诗追随者与诗评家就“何谓朗诵诗”这一重要诗学问题展开了持久深入的论辩,在凝聚共识的同时也碰撞出新的创见与思想火花。本文拟在史料爬梳剔抉的基础上重审百年中国朗诵诗诗体理念的嬗递。
一、“新诗中的新诗”:战时文化语境下“朗诵诗”诗体的理想范式建构
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诗朗诵运动的兴起,人们对朗诵诗的需求逐渐增加,于是关于“朗诵诗”诗体特质问题引发了长久而热烈的讨论。王冰洋认为“朗诵诗是抗战中诗坛上新兴的一种诗体”,受抗战诗歌为广大劳苦群众服务的影响与制约,“形成了一些得之则是朗诵诗,失之则不能成为朗诵诗的特征”,具体表现为:一是内容方面原则上“必须绝对用具体结构有情节的故事为素材”b;二是表现技巧方面要求诗歌综合运用诗与小说的表现手法,以一种独特的“形态史诗”来铺叙故事,同时融入民歌小调或民间演唱物的表现技法,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三是形式方面,语言上要尽量使用经过“提炼洗濯融化”的群众所通用的活态语言,音律节奏上要批判吸收歌谣小调与评唱鼓书的音响结构。四是篇幅方面,朗诵诗的篇幅长短要适中。总之,“可诵性”是朗诵诗的生命之根,是朗诵诗成为一种特殊体裁的标识。
事实上,抗战时期文艺的宣传鼓动效果反向规约着人们对朗诵诗特质的识别与指认。柯仲平认为朗诵诗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内容是真实的,最能感动大众,有高度教育意义的;2.使用的语言是大众化的——一面容易使大众接受,一面却又能提高大众化的言语;3.富于律动的组织”c。隹禾则提出在1938年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朗诵诗还应具有“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的力量:短、紧,活跃像一个大鼓,一颗炸弹,一个春雷”d。在诗为抗日救亡运动服务的时代文化语境中,李广田眼中的朗诵诗有三重面相:一是诗歌融入了属于“大多数人”(集体而非个人)的强烈的爱与憎;二是诗歌含纳“政治的感情”“思想化的感情”或“感情化的政治思想”;三是“用简单明快而有强力的语言”e。陈纪滢进一步阐发了朗诵诗的认定要求:“1.质的方面是富有战斗性的,是现实的,是前进的,不是颓废的;2.文字必须通俗化;3.一定要有韵;4.要附带表情和动作;5.一定要背过;6.朗诵的人应该选择”,应该说前四个要求是针对朗诵诗的,而后两个要求是针对朗诵者而言的,所以“这不完全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上的问题”f。当然,也有一些论者用形象的语言描述朗诵诗,认为“今后的朗读诗,应当是直线条的,粗线条洪钟一般的,响亮的诗歌”,这是从诗歌朗诵声音效果和情绪特征维度来考察朗诵诗的性质,它“不是‘毛毛雨’,更不是‘渔光曲’”,“而成为‘保卫马德里’和‘义勇军进行曲’”,唯有形成“强有力的”朗诵效果的诗方为尚好的朗诵诗g。概言之,在崇尚力的美学效果的驱动之下,感人的内容,明快而有力的“口语化”语言,富于律动的节奏和简短紧凑的诗句,强烈而分明的集体化与政治化的思想情感,是现代新诗成为朗诵诗的鲜明质素、底色与本体。
抗战文艺旨在揭露日军的罪行和鼓舞全民抗战,“诗,从文房中的诗帖,变成群众大会的诗传单,由文士的唱和变成枪弹”h,朗诵诗的传播空间和价值功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韩北屏就认为“朗诵诗的内容,从最基本的原则当然是通俗化,大众化”,至于朗诵诗的形式“除去太深奥的太洋化的形式之外,它的形式都可以试验”,诗句的“口语化”,“不必拘泥于押韵”,“句子不必太短或太长”i。值得注意的是,包括韩北屏在内的很多诗论家都从诗歌的语言形式维度入手识别“朗诵诗”文体,不管是吕骥强调“口语化”和“土话化”,还是朱蓝说朗诵诗“必须是一首通俗化的诗”j,以及常任侠提及的:“关于朗诵的诗,一般都以为要通俗化,大众化,口语化,是当然的,但切忌是标语化”k,都在反复申说语言的通俗之于朗诵诗诗性生成的重要意义。
关于朗诵诗诗体认定最具代表的是朱自清,他虽然没有给朗诵诗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对朗诵诗的性质做过经典概述:“朗诵诗是群众的诗,是集体的诗”,因此语言上要“沉着痛快”,“充满辣味和火气”l,诗行上要简短停顿多,朗诵诗要严肃,要特别注重诗歌的政教作用,只有这样朗诵诗的独立地位才能逐渐确立起来。列车在《诗的朗诵》一文里亦指出朗诵诗语言要“土语写”,诗行上“分节分段”便于朗诵,有韵脚“唱来才顺口,而容易记住”,而且要“创造民族的形式”,认为“我们绝不能把朗诵诗当做新诗中的一门,它是新诗的主体”m。和朱自清看法不太一致的是,列车更倾向于将新诗的可诵化视为新诗发展的一种必然的趋势,朗诵诗与新诗是同质同向发展的,朗诵诗之于新诗的独立性并不成立。
如果说上述的诗论家主要从理论的层面讨论朗诵诗与新诗的区隔,那么以高兰为代表的诗人则从实践出发切入这一话题。高兰说:“诗原本是朗诵的”,“‘朗诵的诗’之被提出,便是给予这种时代的要求,历史演进自然的趋势”,是“为造成一种运动不得不采取的方式”,“同时也并没有固定的分什么是‘朗诵诗’,什么是‘非朗诵诗’”n,“朗诵诗”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文字通俗化;二是要有韵律;三是热烈与现实的情感。这显然是在回望来路,直视今路,展望新路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比较客观公允的辩证眼光审视“朗诵诗”的本质。虽说一些观点与他人不谋而合,但强调朗诵诗应具有感染力的“火热炙热的情感”,以及“与大众有血肉关系的现实的情感”,情感的丰沛性与现实性成为朗诵诗的一大特征,这样就能把“非朗诵诗”——那些写在纸上的歌咏自己私人琐事和风花雪月的鸳鸯蝴蝶的诗,与真正的朗诵诗区分开来。
如果说朱自清、柯仲平、李广田、高兰等是正向建构朗诵诗本体,那么梁宗岱、沈从文和李华飞等则从反向审思朗诵诗命名的合法性。梁宗岱在《谈“朗诵诗”》一文曾强烈质疑“朗诵诗”命名的合法性,他说“什么是‘朗诵诗’呢?有些人——大概是首创者罢——以为这是一种新发明的诗体;后来又有人出来更正,以为我国古已有之;更有人主张‘凡诗皆可以朗诵’的”,“既然‘古已有之’,既然‘凡诗皆可以朗诵’,为什么‘朗诵’可以成为一种有特殊作用的特殊诗体底标题呢?如果‘朗诵’是它和一般诗共通的德性,而‘大众化’才是它的本质上的特征,为什么不称为‘大众诗’而称为‘朗诵诗’呢?”o。在梁宗岱看来,因为人们很难给“朗诵诗”一个明晰合理的解释,所以它不过是一个“时髦的名词”,根本经不起“最短促的时间底冲洗”。随着20世纪30年代诗朗诵运动不断勃兴,梁宗岱对“朗诵诗”命名的探问,其实就是对“朗诵诗”作为一种特殊诗体的合法性审查。的确是如此,凡是新诗都可以朗诵,“朗诵的诗”和“朗诵诗”的边界显得模糊不清,“朗诵诗”的文体特质难以彰显。所以梁氏认为“朗诵”是“一种抒情的,兴奋的,激动的读法”,是“近似说话却又比说话高亢的”读法,因而“接近语言底自然”,“是一切可朗诵的诗的条件”,而“节奏整齐,音韵铿锵”的诗应该视为“吟诵诗”p。“朗诵诗”本质上的特征应该是接近于散文的自然语言与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