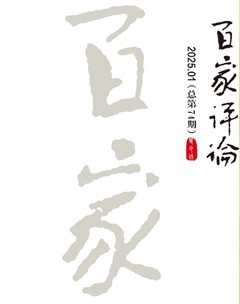内容提要:西渡是当代诗人的杰出代表,已出版《雪景中的柏拉图》《草之家》《连心锁》《鸟语林》《钟表匠的记忆》等诗集。在诗人众多诗作中,赠诗渐成体系,颇值一窥。他的赠诗既保留非赠诗的特质,又因为视点的介入,而将原有的特质复杂化。赠诗是与他者的非在场式交流,通过视点的投出、转向与双向,可以感受到作为现代个体的诗人在人生路途中对他者的呼唤及对自己内心的探究,其文本交涉的对象,无论是外国诗人还是中国诗人,都最终指向对自己内心的投石问路。
关键词:西渡 赠诗 注视 他者
当代诗人西渡的诗具有一种真诚与孤独的特质,这种特质体现于对视点的设置,我们可以在这种设置中感受到诗人的目光投射。在目光的投射中,可以感受到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在苍茫路途中对他者的呼唤,而这种呼唤既来自内心,也最终回归到内心,沉寂下去,成为自己心路沉积的一部分,人生路途所得的一部分。视点在苍茫中投射出去,无论着眼于但丁、戈麦、骆一禾还是臧棣、敬文东、张桃州,都是文本撰写中自己对自己内心的一种投石问路,并通过与他者的虚空交流,得到内心的回响。而德里达同样指出“放弃了他者,就等于自闭在一种孤独之中”。a诗人孤独而不自闭,在我与他者、我与自己之间思索,苍茫的人生旅途因而丰沛。在自我注视下,视线中泛着孤独个体的内心涟漪,交织着西方式的内心探源与中国文化语境之诚。出自立心之本的与他者非在场式交流,回荡在个体建构的诗文本空间中,形成一种独特之注视。
一、一种注视
海德格尔曾经在《林中路》的其中一章《艺术作品的本源》探讨艺术作品的本源问题,一个事物从何而来,通过什么它是其所是并且如其所是? 一件作品何所属?b类似的问题:人从何而来,通过什么它是其所是并且如其所是?或者诗人从何而来,通过什么它是其所是并且如其所是?作为学者的诗人有过很多次思考。c假如艺术作品可从物与人的相互关系中寻求答案,那么人的存在,需要从自身与他者之关联来寻求答案。
诗人对人的注视从早期的诗歌中即已展现。d在1990年,诗人写给但丁的诗有三首,包括《但丁:1290,大雪中(之一)》《但丁:1290,大雪中(之二)》《但丁:1321,阿尔卑斯山巅》。这三首诗在视点的叙述与意义方面非常具有特点:
独自在旷野飘泊多久,在失去你的第一个冬天
这场大雪只为我一个人落下,伸向远方的道路
因而变得更加宽阔而清晰,贝亚特丽契
在旷远的大地上引导我前行,几乎就在地平线尽头
你行走在三千支烛光之上,没有天使紧随
但已足以让我瞻望到天堂的存在,在风雪之上
死亡使永恒有了一个相称的开始
一场大雪,它在我的内心会持续得更久
它的锋刃一直指向明天,我对自己说:
但丁,你要圣洁地生活,……
就像在红色帷幕内部,此刻正酝酿伟大的剧情
整整一个冬天,我仿佛走入一颗密封的心脏
在生长的雪地中,贝亚特丽契,我一生的事业
正在完美地呈现
(《但丁:1290,大雪中(之一)》1990)
诗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1.“引导”一词。在诗歌中贝亚特丽契引导但丁前进,而现实中是诗人在但丁的引导下进入但丁的精神,这是一种引导关系的递进与叠加。2.共生。这里的“我”是诗人还是但丁?从叙述的内容来看,这个是但丁,无论内容还是话语,都指向这个“我”是但丁,如“我对自己说:但丁,你要圣洁地生活”。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我”也是诗人。我在他者的感召下,成为他者,所以,这是一种强烈的共在、共存关系。诗人用一种非直接接触的接触与他者共生。从叙述或从诗人的情感上来说,都是值得注目的一种关系。这甚至不是一种面对面,而是一种直接的融合,我与他者关系的一种全新的关系。失去了“之间”空隙的一种融合,没有中介,没有嫌隙,没有焦虑与恐怖。
这里是不是透露了诗人写诗的初衷?包括:1.受到感召;2.成为他者之欲望;3.对自身世界的省思。诗人在他者精神的引导下,与他者共生,对自己身份暂时弃去。理解这种弃去,可能需要结合诗人其他诗歌一起观看,如诗人此阶段注视外界的目光具有沉痛的特质,如“雪下着。/冰凉而弯曲的刀子/我一直站在它的刃上。”(《雪》1990)“我”的处境非常艰难,站在冰凉而弯曲的刀刃上,如“雨。/黑白铁。归人。镀金铬板。/雪。痛悔这两个字。土豆。/剥土豆的农妇。死亡这两个字。”(《黑白铁十四行》1990)诗人注视外界的“铁”“雪”“土豆”,他想到的是“痛悔”“死亡”这些字眼。相反,在诗人写给但丁的诗歌中,反而呈现出具有抚慰性质的词语“引导”“瞻望”“启示”“伟大”“完美”。可见,诗人注视自己世界带来的痛苦令其目光转向他者世界,诗人通过注视他者来缓解内心的痛苦。诗人在自己的世界中丧失了抚慰,转而在注视的他者世界中寻求向上的可能。
所以,当感觉到“我们注定是孤身一人/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骨头挨着骨头,却素不相识”(《当新生命的啼哭……》1990),诗人注视他者,成为他者,共生,诗人成为但丁,“在无垠的雪地中,我失去了记忆/我的心变得像这冬天一样圣洁,在这样的时刻/我重新获得了祈祷的能力,跪倒在你的面前”(《但丁:1290,大雪中(之二)》1990),在与但丁灵魂共处中,回答了自己对终极意义所产生的疑问:
我恍悟我一直在努力接近死亡
我的一生只有一个可称之为伟大的目标:
在欧洲的最高处死去。现在我达到了,领悟了
却感到空虚,贝亚特丽契的灯
已经在我的内心熄灭,但我知道
人类中那些最杰出者将重蹈我的覆辙
这给我安慰,我在阿尔卑斯山巅微笑
就像阳光下一座白发苍苍的雪峰
(《但丁:1321,阿尔卑斯山巅》1990)
诗人注视但丁的同时,重走但丁的精神之路,现在“领悟了”,自己这种“重蹈”的价值,这是杰出者与杰出者的超时空接触,一种注视也是精神的一种新生,“死亡使永恒有了一个相称的开始”,接近死亡者便是接近永恒者,注视永恒者是领受启示的必经之路,但丁的安慰因而经过视点转移给了后来者——诗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