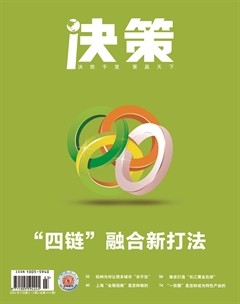1983年,深圳市第一所大学才规划诞生;2000年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简称“深圳先进院”)、南方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鹏城实验室等才陆续建成,深圳医学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投用更是在2020年后。
但深圳的科技创新并未“先天不足”。数据显示,2023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R&D)2236.6亿元,占GDP比重达6.46%,总量、强度均居全国城市第二,仅次于“大院大所”云集的北京。其中,深圳企业R&D经费投入总量居全国第一。
1997年,司托克斯(Donald E.Stokes)以“是否考虑应用”和“是否追求基本认知”为横轴和纵轴,将科研活动划分为四个象限。平衡基础研究与实际应用,努力进入“巴斯德象限”成为城市发展的共识,但各城市科研与创新的起点往往在“波尔象限”或“爱迪生象限”,于是问题产生——如何穿越象限?
在产业升级推动科创能级提升中,逐步从“风险折价”进入到“创新溢价”,认知转变的背后,是创新范式逐渐积累并得以形成。
“上午发论文,下午就有投资人找上门”的故事,在深圳越来越常见。比起“0—1—10—∞”的线性传导,深圳的创新更似一个复杂多维的动态网络,高校、科研机构、企业、投资方等各个节点的创新主体相互交叉、影响,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最终释放产业科技互促双强之“蝴蝶效应”。
新型研发:
“四不像”穿透四象限
1984年,中科院计算所投资20万元人民币、11名科技人员主导,联想在北京诞生,成为国内最早由科研院所孵化的企业之一。
同一时间,作为经济特区的深圳,蓬勃的进出口贸易带动经济高速发展,但全市有且仅有的一所大学——深圳大学建校还不满两年。
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先天不足,使深圳的创新路径从一开始就有别于北京。有经济观察人士总结:深圳不搞学院式、宫廷式的研究,强调企业在技术开发中的主体作用。
若将早期的深圳置于司托克斯的四象限中,它应该在爱迪生象限。从任正非、王传福的创业故事,到90%以上研发机构、研发人员、研发资金等都在企业的“6个90%”创新经验,企业始终是深圳科技创新的主力,市场则是企业研发的唯一检验标准。
“企业创新是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分散决策,大家都要为自己的决策承担责任,因此企业是最讲求效率的组织,能敏锐感知到市场想要什么,并通过有效配置和整合资源,实现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多、最好的研发成果。”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教授陈宪表示。

然而,企业一方面难以接触高水平科研平台与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出于盈利性、规模化生产的考量,开展的注定更多为应用研究。
而随着“深圳速度”带来的规模优势、后发优势发挥至接近极致,“以市场换技术”的路线渐显被动,单一的应用研究已不具备可持续性,如何迈向“巴斯德象限”,是摆在深圳面前的一道难题。
一面强调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另一面,深圳将目光投向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的老牌高校。1999年,全国第一个集成国内外院校资源的产学研示范基地——深圳虚拟大学园诞生;1996年,园区占地规模最大的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成为全国第一家新型研发机构。
彼时,国内对“新型研发机构”还未有明确的概念厘定。“四不像”则是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对自己的定义:既是大学又不完全像大学,既是研究机构又不完全像科研院所,既是企业又不完全像企业,既是事业单位又不完全像事业单位。
凭借清华强大的技术和品牌资源,背靠深圳的产业链资源,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成了一个企业“孵化器”,研究院大楼建成仅一年,企业入驻率就达到90%。截至目前,研究院累计孵化企业3000多家,培养上市公司30多家。
国家层面,直到2021年,新修订的《科学技术进步法》才正式将新型研发机构作为一类法定创新主体写入,遵循“投入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化”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