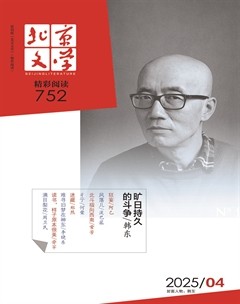各自独立又浑然一体的五篇小说,传递出人生的信条与奥义,更提供了一种新的小说尝试,以拼接、摘录等方式对博尔赫斯《另一段经外经》、威廉·福克纳《插曲》、帕尔·费比安·拉格奎斯特《英雄之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沙里克》等作品进行仿制,展示了小说创作新的可能性。
去年十月,我和另外三名中国作家受邀参加赫塔菲黑色小说节,根据计划,我和其中的君天将于当地时间二十四日晚乘机回国,这天白天原本安排我们俩去参观一家工厂,我们委托对接人阿尔穆德纳·阿纳斯向组委会申请,改安排我们去索菲亚王后艺术中心。
阿纳斯有着今人不多见的驯顺。我们不能说这种驯顺是提供给我们个人的,显然它是奉献给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人或者一群人的。我们这批五十岁上下的人是感知过存在于人身上的信义的。今天,它在人身上普遍失踪。它不是突然失踪的,这里有一个缓慢的过程。我们可以把信义理解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无形但有力的契约。比如借钱,即或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借款人也会赶在一个双方内心认定的日子把钱还上;一个人即便就要死亡,也认为自己有义务回答提问。人们通过回应让对方感到有尊严和价值。现在我们知道,这一切毁了。当出借人意识到款子难以要回来,他就倾向于免除利息,并只索要本金的一部分。借款人也就更把延迟还款、不支付利息以及只偿还一部分本金视作理所当然。往昔,在不往外借钱时,我会承受很大心理压力,因为人家注定要及时还钱,你手头有闲钱,为什么不借?但现在,随着借款人几乎确定不会及时还钱甚至是不还钱,随着古老规矩被践踏,我不再对吝啬心存愧疚。一个人答复另一个人,间隔时间也越来越长。有一些是不会有回答的。你不知道他是故意如此还是只是过失。如果我们对此等待,就会像贝克特笔下那两个流浪汉一样可悲。我们已经很少在他人及自己身上看见就像你打一个电话给酒店前台要什么然后几分钟内它果然被送来一样令人感到踏实的应答了。我们发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感叹、每一个提议、每一项计划),都像哑炮,或者让人忍俊不禁的自言自语。长诗《歧路行》第一章这样写:
逝去的是大海返回的是泡沫
逝去的是一江春水返回的是空空河床
逝去的是晴空返回的是响箭
逝去的是种子返回的是流水账
逝去的是树返回的是柴
……
这里存在返回,虽然返回的是与我们内心期待与坚守的大有落差的事物。怕就怕:
逝去的逝去的是无穷的追问
返回的没有声响
往昔我们不会对阿纳斯这样一个有求必应的人过于感念,对她的付出,不免认为只是她分内之事。但现在却把她视作苦海中闪烁着光的灯塔。或者一根救命稻草。因为上课她在第一天出现后就再未露面,但她用邮件妥善处理好一切。她为我们买好索菲亚王后艺术中心的门票然后让我们去问询处取。这儿的应问者手里抓着我们的票,还看了它,却断定不是我们的。我们从阿纳斯那里得到准信,再次去找她,她又看看,说:还真是你们的。我们和很多人一样,来这儿是为了观看毕加索创作于一九三七年的油画《格尔尼卡》。艺术中心把最好也是最大的一块场地留给它。它获得的荣誉之多,无人能及。每天只要打开门,就会有三排站成扇形的观众面对着它。他们与展品保持一种不能算远但也绝不能说近的距离,仿佛画作会涌出潮水,不站在界线之外,鞋就会被浸湿。如果不是站在第四排除了前边人的后颈和头发什么也看不见,相信还会有第四排。以及第五排、第六排。三排是一个限额,好比餐馆只会有一定数量的桌子。每次只要离开一个人,就会有另一个人忙不迭地补上。永远都是这样,满满当当的三排人,不多也不少。我想到一些百年老店熬制的老汤,每当锅内少了些东西和水,店员就续上新的。永远是那一锅汤。他们在这里久久、久久地谛视,有的在胸前交叉着双臂,有的用拳头抵住下巴,有的盘腿而坐,有的扶着挂不太稳的耳机,有的倾斜着头(既为着听取同伴的轻声讲解也为着目光不脱离画作),有的垂首逼视,有的捂住一边眼睛,很显然是害怕错过什么。不是怕错过几十万年一遇的流星或彗星那样的奇迹,而是伟大事物对自己的启示。一种灵见。一些原本喜欢嬉笑打闹的儿童此时也宛如班干部,投入到严肃的视觉开采行动中。一会儿,有人点一点脑袋,心满意足地离开。他旁边的人往他最后看的地方望去,也有所得,转身离开。有的人用时比他们久却一无所获,不得已也点点头离开。参观之前,我没有去对这幅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做哪怕是最简单的了解。这导致我对他们如此虔敬大惑不解。陈列在他们面前的,与其说是一幅大师的作品不如说是美工草图,没有着色,用的也是漫画或者广告图案那样的画法。是对屠户(或碎尸犯)肉案上的事物的堆砌:断胳膊断腿儿(有的胳膊在被斩断时还保持着呼救的姿态)、一些人和动物的头,诸如此类。我想起一些无法得到绘画训练但又对它保持热爱的人,也能弄出这些象征性的线条。我看不出他们的作品和它存在过大的区别。另外,作品可能利用了规制对人们内心的引导。它面积巨大(长七点七六米,高三点四九米),展厅有着高耸的顶部以及使得回声缭绕的墙壁,这使得观众很难不扔下自己的事,臣服于它。也许,在这儿挂一块银幕或一面破败的大旗(甚至是内裤),也会让人们驻足,为之殚精竭虑地思考。
今天,我为当初不自觉流露出的轻蔑后悔。这是一种惯于在乡下人心底出现的轻蔑。使得他如此的,是在这世界存活的,绝大多数是像他这样的人。这使得存在于他们身上的双重无知——对知识的无知,以及对这种对知识的无知的无知——非但不能让他们窘迫和惭愧,反而成为他们任性裁决世上事物的基础。对自己不懂和不能得到的事物,他们倾向于否定、消解和破坏。既是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威,防止受骗,也掺杂着嫉妒。他们一直在耍赖,却自标敢于说皇帝啥也没穿的可贵的孩子。幸而我在离开《格尔尼卡》时,没有当着观者的面冷笑并口出“就这——”这样的狂言。
二〇一一年,我和杂志主编同时也是策展人欧宁路经东三环,面对央视总部大楼那庞然大物,我不假思索地喊:“大裤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