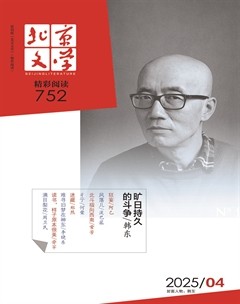一
从《红楼梦》起,寻找儿时旧梦,就成为中国文学的美丽母题。如今,现代化飞速前行,日新月异和翻天覆地之后,追寻与回忆儿时景象更成为“疗愈文学”的共同风格。然而于我,却似乎正相反。因为我童年少年时,生活在煤矿,虽然同样留下许多难以磨灭的美好,但最刻骨铭心、辗转难忘的,是当时煤矿的工伤和工亡。
小学一年级到爸爸工作的山西潞安矿务局五阳煤矿读书,跟爷爷奶奶住在矿家属区西排房7号。6号一家,是妈妈和一女二男三个孩子。两个男孩双胞胎,小我一岁,都长得很漂亮。妈妈个子高、很利索,每天把职工楼的床单拿回家洗,三个孩子帮忙搭,门前一片“只此青绿”。当时矿上女人有工作的很少,我很有些羡慕,问奶奶,奶奶说“咱不能眼气(家乡方言:羡慕、妒忌)人家,是死亡家属。”我第一次听到这四个字组成的词语,很有些难解,不料,却是矿上最常见的群体。
所谓“死亡家属”指井下工亡人员的遗属,包括老婆孩子。矿上政策,给老婆安排工作,通常是选矸楼、灯房、宿舍楼,每月给子女生活费。《平凡的世界》里,惠英嫂就属于死亡家属。作者给了一个温暖而蒙眬的结局,孙少平和师母仿佛结合了。近期到陕西清涧路遥文学馆参观,看视频,说“《平凡的世界》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把笔直接从二楼的窗户扔出去”,姑且不说这动作是否属于“高空抛物”,主要是原作最后用的是“……”,表面符号之差,其实大有深意。
孙少平与师母的结合,是一个美丽的结局,但更可能是一个美丽的神话。就我所知,五阳矿没有一户死亡家属再婚的,倒不是有什么“忌讳”,而是完全出于经济考虑。矿工工作危险,但收入较高,而且每月都有“麦儿黄”,对农村姑娘吸引力很大,在农村找个未婚女子易如反掌。矿区不是“城乡接合部”,而是被农村包围的小城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五阳矿有职工食堂、灯光球场、俱乐部、街心公园,许多家庭住上单元房,用上暖气、自来水、管道煤气,看上闭路电视,和一步之遥的农村生活,简直是两个世界。明显的城乡差别,使死亡家属本人,不愿意嫁到附近农村去。鲁迅有句“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似可描述此种状态,虽然她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知道这两句诗。但也不太彷徨,也没人去土地庙捐什么门槛,煤矿作为工业,尊奉的是太上老君。而且,同样的人多了,就自然了。路遥是善良的,但更是清醒的,他把六颗珍珠平放在地面,看能不能串成项链。
时常,矿招待所门前,一圈人围着,一老一年轻两个女人在号哭打滚,孩子不知所措地站着。不用问,又一个工人在井下工亡了。见多了,并不太震惊难过,认为这就是生活中的常态。可也没有“只是觉得她们吵闹”,煤矿工人之间的悲欢,还是相通的,大家都处于同一境遇。爸爸的几位工友,我两位同学,都命殒井下,死法各不相同。我一位同学极惨,被脱轨的电车挤到巷道壁上,胸部仅厚10厘米。生活表面平淡无波,似乎岁月静好,其实无时不惴惴,担心亲人出事。一次,弟弟没在通常时间下班回到家,我爸说了半句话“要在地面,就知道他耍去了……”
爸爸下井30多年,直到退休那天。“当个地面工”,一直是他的梦想,尤其在工伤的时候。我还很小,爸爸回柱时被顶板上掉下来的石头砸中安全帽,门牙被震掉两个。右手大拇指骨折,终身不能弯曲。有人说,在井下,越小心越容易出事,爸爸说“在井下,就要多小心”。他身高180厘米,却常说“下井要有三分猴相”。工作30多年,爸爸最大当过副组长,好像没得过先进。职工食堂前的“光荣栏”里,经常贴着胸佩大红花的“先进工作者”照片。有次,我看到“栗红旗,采煤六队”,和爸爸一个队,名字还这样好。不料不久就工亡了,和爸爸一个班,刚还在说话,一不留神被卷进机尾……“采一个工作面,要把一个队的人工伤完呢”,由于小心,他几次伤得都不算重。重伤,像腰或腿骨折,就得住院,病房里,净看到腿高高吊起的年轻人。队里派人照顾,专有名词叫“伺候工伤”,属于轻松活。实践出真知,煤矿医院的骨科,水平普遍高。
如今,爸爸77岁,每天喝二两好酒、抽多半包细烟,和妈妈相跟着买菜、遛弯。“父母在堂”,是子女最大的幸福,我们兄妹却心有余悸,幸福之余,更多深感幸运。
二
持续50年的担心,在下到神东煤业集团上湾煤矿综采工作面的一刻,便几乎根本消除了。
听说下井考察,同行作家有兴奋,也掩饰不住一些害怕,我则充满期待。我家三代煤矿人,开玩笑说,血都是黑的,我却没下过井。2019年,陪中国作家长治采风团到五阳矿参观井口,我对矿长说,这对井投产时,我在现场。矿长不相信,“井1984年投产的!”“是啊,当时我小学四年级,拿着花环,和同学们一起边跳边喊‘热烈祝贺,新井投产’。”这对井,成了大多数同学生活的依靠,也有人于此“下饮黄泉”……小时常在井口边玩,可不敢,也不让走得太近,只看到一身黑衣戴着矿灯的工人走进铁罐笼,咣当一声,半人高的门关上,外面栅栏一关,信号响起,绞车转动,人直入数百米地层深处。再上来时,出来的人一身全黑,只留下白的眼仁和牙齿,连吐出的唾沫都是黑的。后来常坐电梯,明白了一个道理,从地面向上升,先超重后失重的,高层次人乘的,名曰电梯;从地面向下降,先失重后超重的,煤矿工人站的,叫作罐笼。古语云“名正则言顺”,从名称,即可窥出差异。
在神东下井,换上橘黄色工作服,防水的。鲁迅回忆学采矿经历时说“抽出水来掘煤,掘出煤来抽水”,地层深处,多有地下水,一个班下来,地下水加上重体力劳动大量出汗,工作服里外全湿。夏天还好,冬天换下来放进柜子,第二天全结了冰,要用体温化冰成水,然后更湿下去。先前,工作服由“劳动布”制成,一种灰色的、粗而硬的布料,有点像帆布。“工作衣”一年发两身,多数人要省下一身日常穿用。年轻人穿着崭新的工作衣回到村里,吸引力立即爆棚,甚至超过“兵哥哥”。部队转业回来,到煤矿也算最好的去处之一,五阳矿就接收过一批对越自卫反击战立功战士,从前线到了一线,还是“协议工”。所以,井下工作服不仅黑、湿,而且破,俗语道:“远看像要饭的,近看是掏炭的。”
绒衣,现在许多青年人都不知为何物了,却一直是煤矿工人的“小绵袄”,比棉衣薄而紧致,约半厘米厚,非常暖和。同来采风的黄亚洲老师采访神东三代矿工之家,有诗句“白天,矿井抱着老汉;夜里,老汉抱着她”。黄老师不知道,煤矿24小时工作制,工人三班倒,没这么规律的生活。而且,矿井四处是危险,真正让工人感觉温暖的,就是这身绒衣。见绒衣如见故人,淡墨绿色,也许,爸爸当时穿的也是这种颜色,但我见到的,都是被煤尘和汗水浆过的黑。蹬上长筒水靴,挂上自救器,戴上安全帽,每个人都成了将要出征的特种兵。忽然发现,安全帽上没有头灯。头灯拿在手里,随时可以插到安全帽上,也可以取下来,用的是蓄电池,再不用灯房女工往电盒里注硫酸发电了。
我问陪同人员,上湾矿是竖井还是斜井?答曰斜井。“埋藏多深?”“不深,400多米。”400多米还能用斜井,建井技术可谓高超。煤矿战线的旗帜,潞安矿务局石圪节矿,井深137.45米,依然是竖井。斜井,不用罐笼,一般坐电车到工作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