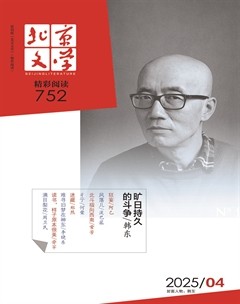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据说,每年的这一天,会有100多个国家举行活动,旨在提醒人们重视读书。
其实,读书,就该像饿了吃饭、冷了穿衣一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还要举办活动去提醒?!可见,读书的重要性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试问,有“世界吃饭日”“世界穿衣日”吗?没有!
一
我在杭州工作时,办公楼紧挨着市青少年文化宫。一到晚上,文化宫广场上就挤满了接送孩子的家长。这些孩子,大都报的是特长班,什么钢琴、提琴、芭蕾舞、跆拳道、书法等等,不一而足。
看着忙活了一天学业、还要被各种培训班折腾得哈欠连天的孩子们,我很是心疼。
有位在媒体工作的朋友,几年间,不独晚上、连双休日几乎也给孩子安排得满满当当。夫妻俩还分了工,你周六、他周日接送。
有一次,我问他们:“这样密集安排,孩子平时有时间看课外书吗?”夫妻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摇了摇头。那位当父亲的说:“趁着可塑性最好的年龄段,还是先要她学会各种特长。看书嘛,将来有的是时间。”
我很扫兴地说了这么一句:“与其费这么大劲、强令孩子学那么多将来未必用得着的特长,不如引导她养成爱读书的习惯。”显然,我的话,他们并没有听进去,直到我调离杭州,两口子还在乐此不疲地给孩子报这种班、那种班。
其实,我这么说,并非没有走脑,完全缘于生活实际。扪心自问:那些所谓的特长,后来生活中真的能用得上吗?成人的世界里,哪个不在为生计忙忙碌碌?!
你想一想,朝九晚五,陀螺般旋转了一天本已疲惫不堪,还要在堵成乱麻的马路上心急火燎、一步一挪赶去接娃;好不容易拖着灌了铅的步子进了家门,这时会是怎样?恐怕连鞋都懒得换,就会一头歪进沙发里。谁还有心情打开琴盖呀?!
有一位朋友,小时候曾在少年宫学了好几年小提琴,还获得过市少年比赛的冠军。我问她现在还拉不拉琴?她说已经三十多年没有摸过了。
而养成读书的习惯,那是会受用终生的!读书,一旦沉浸,会成瘾、成癖、情不自禁。内心的那种强烈冲动,会逼着你像海绵吸水一样不断地去汲取知识。
明代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里讲,小时候因为家里贫困,没有办法买到书来看,“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
他写的这个细节,给我印象很深:“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
这是肺腑之言啊!大凡爱读书的人,恐怕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一位业内知名度很高的同事告诉我,他下乡当知青时,只要听到哪个村有本好书,下了工,再累,也要翻山越岭跑几十里山路借了来读。
记得我能懵懵懂懂读小说时,还是“文革”后期。有一次,无意中知道家里还有一本“毒草”《三家巷》锁在柜子的角落里。我想方设法“偷”了出来,在被窝里借着手电读了一遍又一遍。周炳、陈文雄、陈文婷等人物的命运,从早到晚牵扯着我的心。
后来,听班上一位同学说,他家里有这本书的姊妹篇《苦斗》。我大喜过望,希望他能从家里“偷”出来,并保证绝不折页、绝不损坏分毫。
可这位同学,胆子很小,我软磨硬泡,他始终不敢付诸行动。最后,我以一个弹弓、一个塑料铅笔盒和一大把大白兔奶糖为代价,总算说动他撬开了箱子。
谁知刚看了一半,他的母亲晒被子时发现了状况。于是,这位同学被他的父亲揪着耳朵胖揍了一顿。书,我也只好乖乖奉还了回去……
二
说到读书的好处,那可就大了去了!
窃以为:读书,能让你眼前世界的维度扩大、扩大、再扩大,让寻常柴米油盐的日子,有了韵致、有了美感。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怕黄昏忽地又黄昏,不销魂怎地不销魂”“玲珑骰子安红豆”那种摄人心魄、入骨相思的尔侬我侬,只有读了一肚子唐诗宋词的人,才能体会得出。
而“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这般请缨无路、报国无门的志士之愤,也只有辛弃疾、陆游这样的大才子,才能体会得更加深切。
二十多年前,我在新疆驻站。那时候,交通还不像现在这么便利,无论是去南疆还是北疆,在路上一走就是一整天。
每次出发前,我会把沿途要经过的地方都发生过哪些历史大事件、都有哪些名人吟咏,一一记在笔记本上。于是,一路单调的灰黄里,便有了更多的色彩。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车过交河古城,风沙昏暗中,那清晰的打更声和远嫁乌孙公主的幽怨琵琶声,似乎不停地敲击着我的耳膜。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站在乌拉泊古城,在“胡天八月即飞雪”的旷野里,我和岑参豪迈地进行着交流。
后来调任杭州,满湖的文化遗存,又让我体会到“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之外更有韵味的西湖——
办公楼,紧傍着环城西路。而环城西路,就是白居易笔下的白沙堤——“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昔日,白乐天曾多少次打这里纵马驰过?
办公楼右侧石板巷的尽头,就是孩儿巷。当年,陆游也曾在这里度过春寒。那首《临安春雨初霁》就是在小巷里写就的:“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站在办公楼顶,遥望着孩儿巷,我神游八荒:谁能借来小巷杏花的清香?谁能销去放翁那满腔的幽怨?
办公楼前百余米处,那座不起眼的飞檐瓦舍,就是苏东坡笔下的望湖楼。一天中午,我在白堤散步,突然间,狂风大作暴雨如注。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到飞檐下避雨。面对着湖上的风光,苏东坡那首《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便脱口而出:“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办公楼南面,是南宋大理寺旧址。岳飞蒙冤的风波亭,就在马路的对面。“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岳飞就是在这里仰天长啸“一命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