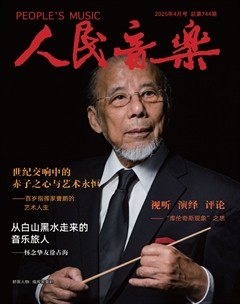贝多芬《第三“英雄”交响曲》(Op.55)是世界交响音乐中的一部伟大杰作。这部作品作为古典音乐中的必修内容贯穿学习过程的不同阶段,每一位接受音乐教育的人必然会对它进行研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也足以证明,《第三交响曲》在“贝多芬学”中始终被当作古典主义作品中的典范。在音乐史学、曲式学的教材以及专门的学术论著里, 已经对其第一乐章做出过曲式分析,对该乐章的结构及主题的认识在不同作者的论述中不尽相同。我们知道,贝多芬作品的结构非常严谨,每一个动机、每一个小节都被赋予了极其合理的规则。正因如此,“贝氏”作品被所有时代的曲式学理论奉为标准。
贝多芬《第三交响曲》第一乐章同样被极其严格的结构逻辑所控制。但是,在分析中可以发现,这种规整性展现出的并非成熟的奏鸣曲式基础,而是以远早于奏鸣曲式形成之前就已存在的古希腊演说辞布局为结构依据。经过古代演说家与哲学家千锤百炼的古希腊演说辞布局,在数千年间被认为是所有表达形式的结构基础,其中也包括音乐艺术。音乐史每一个时期都会从演说辞各部分完美的整体“排列”中汲取必要的逻辑关系并运用在实践中。随着辩证法时代的到来,以及18 世纪文化中对于对比性的关注, 出现了以包含演说辞所有组成部分的整体布局为基础来构建曲式的思想。
约翰·马特松(Johann Mattheson)关于音乐理论与作曲法的论著《完美的乐长》(1739)譺訛是明确表述这种思想最重要的成果。在书中,作者建议作曲家在作品创作中使用古希腊修辞布局。为此, 他几乎没有变动地列出了演说辞的次序:
1.Exordium+-+开场白
2.narratio+-+陈述、描述
3.propositio+– 确立话题
4.confutatio+-+反驳异议
5.confirmatio+-+证实中心思想
6.peroratio+-+结论
当然,这个基本纲要中缺少了几点。重要性较低的话题分述(partitio)与离题(digressio)未被列入(离题也可以转移到布局中的其他部分)。但是,这里还缺少了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在演说辞中占比重最大的论证(argumentatio)。它在此前就已经成为音乐发展手段的原型,远远早于马特松的著作。显然,正是由于它早已广为人知,而未被列入马特松的序列中。
对贝多芬作品的分析显示,即便是称为附属部分的段落也被作曲家赋予了必要的结构意义。这些段落同样受到作曲家对音乐布局的制约,因此也遵循古希腊演说术为作曲家服务的普遍规则,而且这些规则均是作曲家已熟知的知识。德国理论家福克尔(J. Forkel,1749—1818)在其《音乐通史》中将拉丁文的演说辞布局转为对应的德文。这部著作中所陈述的演说辞已经具有了后世音乐家所熟知的奏鸣曲式的轮廓。结合演说辞布局原本的结构与福克尔的德文翻译,将所有拉丁文名称(但没有argumentatio)译为俄文,得到下面这个确立下来的古典(成熟)奏鸣曲式呈示部的总体布局:
1.exordium–开场白(вступление)- 引子
2.narratio–叙述(рассказ)- 引子的延续
3.propositio- 话题确立(определение темы)- 主部主题
4.partitio- 话题分述(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е темы)-连接部
5.confutatio-异议与对异议的反驳(возражение и опровержение возражения)- 副部及副部中的转折
6.confirmatio-8证实(подтверждение)- 结束部
7.digressio-8离题(отступление)- 主题中和的部分
8.peroratio 或conclusio-8结论(заключение)- 结束部的终结
这一逻辑同样形成了贝多芬所有钢琴奏鸣曲(除“奏鸣- 幻想曲”之外)、交响曲以及其他一些作品第一乐章创作中的思维方式。
从音乐的视角来看,转入器乐领域的演说术“发音腔调”(интонация) 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值得我们关注。
1.开场白,运用号召的腔调:“参议员”“士麦那居民们! ”
2.叙述,运用陈述的腔调:“那么,我从这个问题开始……”
3.中心话题确立,运用肯定的腔调:“要知道事情是这样的……”
4.话题分述,运用阐释的腔调:“……罗马人民的荣誉陷入危机,……财产面临危险……”
5.驳论譿訛,在前半部分使用怀疑的腔调:“但可能有不同的意见……”; 而后半部分则是对疑虑进行反驳的腔调:“这里可怕的是什么———远离有害的娱乐并转向有益的工作? ”
6.证实,运用情绪高涨的坚毅腔调:“去变得伟大、强大而且声名显赫吧……”
7.离题,运用偏离主题思想的腔调:“……甚至到现在还给我搞更加卑鄙的阴谋……”
8.结论,用来结束主要思想:“对我来说,目前只有这一个有益的措施。”
但是,贝多芬的修辞结构不仅仅展现在上述每一项“腔调”的意义中,同样也体现在为此而进行的音程选择与乐队中的乐器选择上。这种“腔调- 音程- 乐队”的布局在《第三交响曲》中极其严谨,如同放置在音乐形式基础之上的“隐性演说辞”,只是后来被称为“奏鸣曲式”了。
贝多芬《第三交响曲》作为音乐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新型交响曲体裁的出现:这种规模庞大的作品为后来马勒、肖斯塔科维奇的哲学式巨著铺平了道路。当时,在贝多芬同代人的眼中,这样的作品实在太庞大了,听起来过分冗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