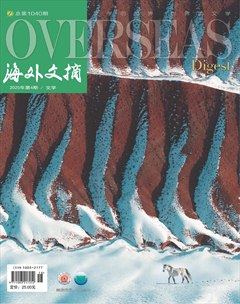1
这无疑是一片废墟。
层叠堆放的砖头,破败不堪的墙垣,横七竖八的朽木……如此凌乱的现场,像一个被残忍肢解了的生命体,裸露在城市的郊野,在冬日的寒风中瑟瑟发抖。我有点儿不忍心直视它,然后小心翼翼地走到它身边,试图快速地逃离过去,去往它前面的那方水塘。
但是一根粗壮的朽木直挺挺地横过来,突兀在杂乱的砖瓦和野草上,把一片竹林掩映的小径也挡了大半,宛如城市居民小区的拦门杠,挡住了脚步,也吓了我一大跳。
我只得俯下身子,想挪开这根朽木,腾出一个可以放脚的地方,去往那边的水塘。可是就在我搬这根朽木的一刹那,我惊讶地发现了这片废墟的秘密。
因为这根木头不是一般的木头,在其最正中位置,依次等距离地分布着六个硬币,分上下两面。每个硬币都用一块红布包裹着,当然,那红布已经完全枯朽。
硬币是先用红布包好,然后用钉子钉上的。虽然钉子也生锈了,但我还是不敢大意,一点点地拔出来,连同那些枯朽的红布灰。我想仔细辨认硬币的年代,但是模糊不清,大约是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约莫也有四五十年光景了。
毫无疑问,依据我多年蜀地乡村的生活经验,这根木头正是这栋房子的横梁,是整个院落的脊骨,就像家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辈,是子孙后代无与伦比的敬仰。
废墟周围还栽种着几株粗壮的枇杷树,枝繁叶茂的样子,地上有很多小枇杷苗正蓬蓬勃勃地生长着,也不知它们究竟经过了多少次的花开花落,才有这树的繁衍和生息。那棵虬枝苍劲的核桃树,看起来更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用无声的语言告诉我:这是一户乡村人家,这曾是主人温暖的家。
废墟前面是水塘,坝埂上巴茅草丛生,此时几个男人正蹲在那里钓鱼。我想,以前水塘里应该还有鸭子,或者鹅,总是在每一个春天来临的日子,拨动着清波,感知着春天的讯息。
我呆呆地望着废墟,再也没有心思去看先生钓鱼了,干脆一屁股坐在一块砖头上。这冰冷的天地,这荒芜的废墟,我似乎总想和它好好地聊一个关于什么的话题。这样的废墟,对考古学家来说是没有多少价值的,但它却是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生活过的痕迹,不管什么原因凋落,都是带着人间温度的,在心里是被珍藏的精神财富。
就在那个时候,废墟被冬日的暖阳爱抚,仿佛在时光的隧道里复活,就像是一颗落地就发芽的种子,在我心里迅速地生根、长叶、开花……
人的一生,不管身在何处,我们脚下的土地是相连的,它就是血脉,能传递彼此之间的情爱。
2
老屋真的很老了。
老屋之后,在一片茂密的竹林下,父亲静静地安息着,他住在那么小的一个地方,却尽可能地给我们修建了几间能遮风挡雨的大瓦房。
老屋的“老”,主要体现在屋基上,就像一个家族的根和魂。父亲排行老大,结婚分家后,他就在宅基地边修建了这几间房子。哥哥姐姐和我都在这里出生,老屋听见过我们的第一声婴儿啼哭,也听见过我们送别父亲那撕心裂肺的哀号。
父亲走了,但是老屋还在。如果从空中俯瞰,它一定像一枚黑灰色的纽扣,牢牢地钉在一片葱茏的乡野之中,显露着生命的气息和活力。
我时常捡拾岁月的胶片,仔细打量一幅永不褪色的乡村风情画卷。瞧瞧,贴在墙根上,是不是已经听见了老屋的低语?看看,房屋的墙根是用条石垒砌的,上面有很多匠人敲过的纹路,闪着古朴的色彩,也透出匠人的巧思。石头们不但稳稳地承载着一墙之重,还敞开怀抱,接纳地虱、蚂蚁们等在罅隙里安家生活呢。
地虱、蚂蚁们每天忙得不亦乐乎,成为我心上的邻居。童年最爱干的事儿之一,便是邀约小伙伴喂蚂蚁。先找根竹竿,在顶端用竹枝缠绕成圈,把蜘蛛网粘上去,然后悄悄躲在屋檐下,只等待飞来飞去的蜻蜓落网。
那些肥实的蜻蜓大腿肉,是蚂蚁们的最爱。当我们把这些诱人的美味放到蚂蚁洞口,嘴里不停地唱着“黄丝黄丝马马,请你家公家婆来吃嘎嘎(肉),大路去,小路来,吹吹打打一起来”的歌谣时,蚂蚁们就会倾巢而出。
蚂蚁家族的团结精神,一直感动着我整个的人生。它们浩浩荡荡而来,个头大的走前面,气度不凡,宛如将军般,指挥着属下齐心协力将蜻蜓拖进洞口。
顺着蚂蚁洞向上,是历经风雨剥蚀的墙面,那是用黏土一点点夯筑的,也有一道道横着的纹路,里面还夹杂着竹篾和稻草等东西,让墙体更加牢固。在没有现代科技之前,祖宗们总是用自己的智慧解决生活方面的难题。
那时候,我总是疑惑,为什么偶尔还能在墙体中发现几个小贝壳呢?或者鹅卵石之类。土墙像一幅挂着的版画,总给人无限想象。后来长大了,学了知识,才明白我们生活的地球奥妙无穷,才恍然大悟,原来故乡可能是海洋!
土墙紧致厚实,像一个敦厚的长者,任凭时光和风雨吹打。它的宽容,纵容了一些生物的放肆,于是在屋檐处总能发现一张张蜘蛛网。蜘蛛们把家安在这里,反正背后有土墙做靠山,风来雨来都不怕。
但是蜘蛛怕我们。小时候干活儿,打猪草、砍柴……磕磕碰碰,总免不了受伤。大人看见我们身体哪里出了点儿血,根本不用惊慌,到墙角屋檐找一只蜘蛛,摁住,拍死,贴在伤口出血的地方,用蜘蛛网包住,然后交给时间去治愈。
所以从小到大,对蜘蛛我都心怀感恩。那时候故乡重庆还没有成为直辖市,隶属于四川省。在重庆话中,我们把“蜘蛛”叫作“bo si”,把“蚂蚁”叫作“mayin”,把“蜻蜓”叫作“mi mi yang”……总之很土,就像老屋的土墙。
土墙之上的屋脊,因西南地区多雨水,中间高两边低,有利于疏浚。居中则一定要选用上等的木材,通常最大、最粗和最好的那根木头,就成了顶上梁。
仰望横梁,它们就像鲫鱼的背脊,两边房屋依次排开去,颇有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