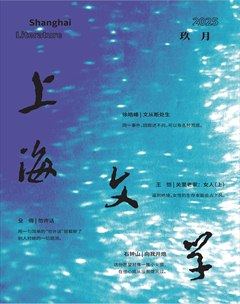1
稳固的社会结构,必定产生稳固的人生结构,几乎所有人的轨迹都类似。姥爷老家玉田西轩湖店村的人们,没有例外的轨迹,就是生老病死、传宗接代。在广阔的生命地图上,他们是一个个微小的点,逐渐构成一条线。线画多了,成了一团乱麻,像小学课堂上偷摸的涂鸦纸张,默默团成一团,扔在垃圾篓里。
这些乱麻一样的人生命运,画在华北乡村的土地之上,连痕迹都没留下,层层叠叠的。一百年来,这个县城也没有什么大人物纪念碑留下来,是平淡的生和死,大地静默,亘古不变。
男人女人都一样,女人们尤其一样。男性还有出走的机会,而女人则默默地生下来就是“别人家的媳妇”,嫁过去之后,就是劳动力,无论在地里,还是家里,乃至炕头,都是一种“生产装置”,没有例外,除非,你生得特别美。
我姥爷的妹妹,也就是我母亲的大姑,小名葡萄,是他们家的美人。美到什么地步呢,说是惊天动地有点夸张,可确属民间传奇,十六七岁就被隔壁丰润县的田姓县太爷看中,亲自登门前来为他家的孩子求娶,旁人眼中真的一步登天,就此摆脱了贫困的家庭出身,进入了本地“豪门”。我妈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回乡的时候,也去隔壁的丰润县窝洛沽镇的豆庄子看过她的大姑。大姑家已经彻底败落,只留下一处宅院,但依然高门大户,有青石砌成的两层台阶,残留着某种富户的痕迹,不像别人家的门槛是浅浅的一道石头。就算都是在贫瘠的乡村,建筑还是有等级差,寓意着背后的身份。人类始终生活在比较之中,尽管最后都是空虚。
看上世纪八十年代县志,说玉田住宅,“富有之家,石基高墙,磨砖对缝,前后挑檐,天井宽大,与城镇类似,多有门楼”。我母亲应该看到了大姑家的门楼,不过到一九七六年,附近的唐山地震,玉田无论城乡,留下的老房子没有多少。
我妈奉父母命送钱送东西,大姑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穿着月白色的褂子,打扮得干干净净。头发梳成髻子,插一簪子,在当时的乡村妇人里,也是别具一格的美,并不显得特别苍老。
在葡萄嫁过去的那天,似乎还有无穷无尽的青春等着她挥霍。她美得素净,并不是那种艳丽的年画上的美女,看上去舒服。从玉田县的西轩湖店村,到隔壁丰润县的豆庄子,说起来只有八里路,并不算远,可轿夫们特意绕了十几里地,走到窝洛沽镇的镇上,再回到豆庄子的青砖瓦房的大宅子,走得极为张扬,让人们看看田家的二少爷娶了个远近闻名的美人。正是盛夏,田地里麦苗结籽尚未坚实,可是为了她的婚礼,家里还是极力铺陈,把青色的麦穗采摘下来,请客吃了平日舍不得吃的“粘转”。我妈说,她五十年代回去的时候,赶上吃了一次,用新下的蒜苗炒粘转面条,是华北农村的美味。
我姥姥边在厨房给她操持,边和她说,这在玉田乡下,是“不会过”的人家才这么吃。乡下的饮食困窘,生活单调,和食物也纠缠起来,一个吃的也有很多讲究。青色的麦穗里水分多,铺张的人家才舍得吃。将炒熟的麦穗磨成粉的时候,香气扑鼻,婆婆会在旁边监督媳妇,害怕偷吃。我妈和我姥姥说,要是她在磨房,估计没磨完,都被她吃光了,姥姥笑着说,傻孩子。那是我母亲少有的清闲时光。
农村生活有很多这样关于吃的典故,说是有个媳妇因为偷吃热豆腐烫死了。在厨房偷摸着吃滚烫的,怕婆婆看到,非常诡异而残酷的饮食轶事,就是为了说明刚做好的豆腐滚烫?背后可能还是各种家庭戒律。
我听了“粘转”名后大有兴趣,因为在张爱玲的书里和乾隆皇帝的菜单里,都看到过“粘转”。张爱玲的《谈吃与画饼充饥》里写到这种食物:“我姑姑有一次想吃‘粘粘转’,是从前田上来人带来的青色麦粒,还没熟。我太五谷不分,无法想象,只联想到青禾,王安石的新政之一。我姑姑的话根本没听清楚,只听见下在一锅滚水里,满锅的小绿点子团团急转——因此叫‘粘粘(拈拈?年年?)转’,吃起来有一股清香。”
张爱玲的乡愁,是标准的都市人的,在遥远的海外回忆这种传说中的家乡食物,虚无缥缈,我看的时候觉得就是煮麦粒,不觉得是什么好吃的。没想到,在乾隆下江南的菜单里,有更符合历史事实的“粘粘转”的做法:乾隆三十年四月,在山东夹马营和马头营一带,下江南途中,皇帝吃到了“粘转”,是那个年代北方民间稀罕的食品,宫中也有进贡,这次应该是季节凑巧,下面人也凑趣逢迎。
乾隆关心农事,下大雪滋润了土地,一定要写诗,碰上新麦抽穗,自然也不会放过。这种食品的准确做法是用新麦穗煮熟(或者炒熟),剥去壳,然后磨成细粉,顺着石磨盘流出来的,下进滚烫的锅里,是一碗清香的面条,叫“粘粘转”,也叫“碾转”,应该是象形命名法则,粘粘,其实是石磨旋转的样子。
刚收下来的麦子远不如结实后饱满充数,只是吃了个清香,吃这种食物的人家,往往有种“不过了”的豪气。
大姑是姥爷家的传奇,她是被权势的家庭挑过去传宗接代的。据说丰润田家相看了不少人家的闺女,最后听说隔壁玉田县不远的西轩湖店村里王起家的姑娘美貌,不仅媒人上门了几次,后来二少爷也亲自上门相看,类似情节,《聊斋志异》写过无数次,眼见为实,才首肯了这门婚事。而我姥爷家自然求之不得,在贫困系统里挣扎的一个普通家庭,最不济,也是给自己家的女儿找到了一个好去处,更何况,田家下的正式聘礼中,还包括了给姥爷家的土地,正儿八经的好田若干亩,王家从此成了有地的家庭,邻居羡慕不已,“要发了”。
我姥爷有两个女儿,我大姨和我母亲,都算得上模样端正,可我姥爷总说,你们比起我大妹妹,那是差远了。华北乡村大约照相术还不普及,实在没有她的照片,一切只凭想象。但现实的残酷,却让所有人的美梦落空,大姑的美貌,完全没有给她带来福气,只有真实世界的冷酷如铁。
刚嫁过去,有点新婚的快乐,大姑回娘家,絮絮叨叨聊琐事,说到大户人家,规矩繁多,公公婆婆考较她的女红,她是怎么蒙混过关的。县太爷把两个儿子的媳妇叫到跟前,叫他们连夜给公婆分别裁剪几套褂子和裤子。大姑在家只学过纺线织布,并没有上手过多少针线活,她和她的妯娌在一间屋子里准备,她的大嫂说,你快回屋去做吧,否则来不及,大姑说不急不急,一边偷眼看着她的嫂子如何裁剪和缝纫。她大概是个聪明人,眼见着就学会了,下半夜自己回房间,似模似样地把服饰裁了出来,居然也没出错。公婆觉得这个媳妇合格,对她很是看得上,回娘家一次,带回来的吃食,能让娘家人欢喜几天。这是我母亲的奶奶给她讲的故事,婉约的乡村小品。
可以想见葡萄讲述乡村“豪门恩怨”的小小得意的样子,乡下姑娘,嫁到这样的人家,也算一步登天。我姥爷说大姑是“玻璃人儿”,像《红楼梦》里李纨称赞王熙凤的“水晶心肝玻璃人儿”。再次和他的两个女儿说,如果她上学,比你俩都强。
这么一个有着玻璃心的美人儿,嫁过去之后,立刻面临着只有富贵家庭才有的问题。那是大烟流行的年代,田家的二少爷就有“烟霞癖”,葡萄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怎么就命该如此。我母亲说不清她大姑父这个习惯是怎么来的,是在他父母活着的时候已经公开,还是在他父母走了之后才彻底地、放肆地、不管不顾地抽了起来。也许,他父母为他找了个农家姑娘,本身就是希望朴实的她,能够约束一下懒惰成性的儿子?更有可能,门当户对的人家知道他家少爷抽大烟的毛病,拒绝婚配,才在贫家选择貌美的姑娘?
乡村传奇的背后,经不起任何仔细的打量,像一种朴素的柞蚕丝的丝绸,表面上平滑,背后疙疙瘩瘩。在老挝旅行的时候,低矮的木板搭建的作坊里,看到他们不知疲倦地纺织着柞蚕丝的围巾,专门卖给游客。中国丝织业发达,这种粗糙的纺织品已经没有容身之地,只有在偏远的东南亚还能找到。那背后打结的丝疙瘩特别多,倒也成了工业时代的手工特色。
不知道大姑嫁到这样的人家之后的感受,大概也是认命。公婆在的时候,丈夫抽大烟,毕竟家里还供得起。
相比起嫁到附近庄上的她的亲妹妹,她至少是殷实的、展样的、值得羡慕的命。我母亲的二姑姑,说是个子高,身体壮实,嫁过去之后,就被支使下地干活——普通农家,家中劳动力有限,女人一样需要干农活——在生头胎的时候就难产而亡。甚至这种苦难也并不稀奇,是乡村女人们的普遍命运。她们的一生如果有旋律,也是乡村单调的唢呐,一股劲地、昂扬地、高亢地悲嚎着,只有家里人惋惜一阵,此人的一切就宣告结束,没多久也被忘记了,就像她没在世间活过一样,稀薄得连点影子都没有。想起村子里被带去看的祖坟,远远地,在青天的外边,和远处的高速公路连成白亮的一条线。之所以有乡村坟地,这还是土地充足的河北乡下,不过几代以上的坟墓,大约也早就挖掉了。
田家父母,也就是昔日的县太爷夫妇去世后,田家的兄长做主,把家产分了两份。我妈问她大姑,那不是欺负你们?五十多岁的大姑说,分得很是公平。田家的大哥也是体面人,加上心里明白,知道弟弟这么抽烟不是了局,在父母去世后迫不及待分了家,无论是田地还是房产都是对半分,在豆庄子,大姑家也有良田近百亩。大姑也是心里明白大伯子的心意,可哪里架得住自己的丈夫放开抽大烟,父母去世更没有了约束,只有几年,田地就去了大半,最后只剩下自己住的房子,也就是我妈五十年代去看到的青砖大瓦房。
此时,大姑显示出了自己作为乡村女性的某种持家本能,严守家产,家里的一针一线都不让自己丈夫往外搬,坚壁清野,她自己带着两个孩子煎熬着过。我妈还记得,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女孩叫小篮子,男孩叫小秃子,都是贱名——乡村的习俗,据说这样才能活得长久。田家的二少爷被赶出家门,一回来,她就往外赶人。
葡萄的彪悍劲被激发出来,她的瓦房,一直到五十年代,连块砖头都没少。田地是卖光了,但过了几年居然逃掉了地主帽子,大姑说这可是修来的好事。大伯家就倒霉了,划成地主。我五舅发议论,“祸兮福之所倚”。
一九三〇年左右,我姥爷已经发家,从东北坐火车回唐山,和我姥姥带着他们十岁左右的大女儿,也就是我大姨,从关外的新家带回大量的现金,准备在玉田老家买房子置地。姥爷姥姥穿着水獭皮领子的皮草大衣,住在唐山最好的客栈里,叮嘱我大姨说,他们出去买点东西,让她不要出门。
大姨闷头在房间自己玩骰子,没多一会,房间门被敲开了,是田家少爷,也就是大姑父。我大姨回老家多,认识他,惊喜叫道,大姑父你怎么来了!大姑父说,你爸妈呢?我大姨说,不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