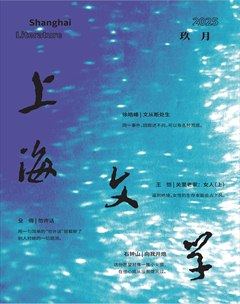有一种人之常情,就是喜欢有趣的人。
有趣的人很洒脱。战国庄子,老婆死了,他敲着瓦盆唱歌;自己要死了,安排后事时让弟子不必埋他,说:天地为棺椁,日月为双璧,星辰为珠玑,万物做殉葬,“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生就自然而然地活,死就自然而然地归,用不着伤感,也用不着留恋。坦坦荡荡,无忧无虑。
这样的自在自然也会让周围的人自在。
有趣的人重情义。汉朝荀巨伯探望重病的朋友,正赶上胡人攻打城池。朋友让他赶紧离开,他说,我岂能贪生而毁道义?胡人杀进城,问荀巨伯:整座城都逃空了,你为什么不逃?他回答:朋友重病,我怎能扔下他不管!
胡人惭愧,竟不取城池,敛兵而去。
有趣的人有风骨。我的晋朝同乡陶渊明受了官场的窝囊气,撂下县令的大印就回了老家,一面做他的老农民“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一面做他的田园诗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老友们纷纷带着酒来见他,一帮人醉得七颠八倒,胡言乱语,没大没小。
有趣比颜值更有魅力。晋太尉郗鉴让管家去丞相王导家挑女婿。管家回来报告:王府子弟个个好,只有东厢房一小子,袒胸露腹,不理不睬。郗鉴说:就他了。
这“小子”就是王羲之。成语“东床快婿”由此而来。
有趣的人慷慨。阮裕有一辆豪车,谁都可以借用。有个人想借车为母亲送葬,不敢说。阮裕知道后叹道:我有车别人却不敢借,那要车干吗?一把火把车烧了。
有趣的人喜欢自然。有年春天,王羲之请了一帮名流雅集兰亭溪边,将盛了酒的觞放在木盘里,顺水漂流,流到谁面前,谁就作诗。
这便是“曲水流觞”。之后便有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有了山水诗、山水画、山水书……
有趣的人有癖好。山阴一道士,为了打动王羲之,养了一群白鹅。王羲之见到这群白鹅,眼睛都直了。道士说,您若想要,就替敝观写一卷《道德经》。
王羲之当即提笔书成书法史上著名的《换鹅帖》。
上述的古人一个个活出了洒脱之美、情义之美、风骨之美、直率之美、人格之美、自然之美、癖好之美……他们全力追求“内不以自欺,外不以欺人”,全力追求“向外发现自然,向内发现深情”(宗白华),不仅自己活出了趣味,还创造了有趣的时代。
《老曹你好》
我的同行朋友中,有几位特别有趣,有机会见他们,我总是满心欢喜。
一位是河北作家贾大山,中国作协第五期文讲所的同班。他不开口则已,开口必让人捧腹。记者拍照,一位山西作家笑得合不拢嘴,一边的贾大山冷冷说:照片可是彩色的。山西作家立即闭嘴——他的牙齿因为醋和烟黑黄不堪。
一位是黑龙江作家阿成。他早年当过跑长途的司机。广袤辽阔的北国大地,笑话是解乏解闷最好也最方便的方式。长途车司机个个是笑话篓子。
一位是湖南作家彭见明。他在县花鼓剧团当过美工,模仿剧团的各色人等惟妙惟肖。一个跑龙套的演员不识字,从小跟着师傅学戏一字一板不敢走样,摇着马鞭“锵锵锵锵”走完圆场,来到城门下,一抬头,念白:“只见门楼上写着一个字:潼关!”说“一个字”的时候还伸出一个指头比画一下。
许多作家说笑话都是现编,张口就来,脑子转得快极了。那些不假思索的绝妙对答反应之迅速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被人当众造谣,只能张口结舌,脸红脖子粗,等想到辩诬的话,已经时过境迁,只好用“不跟小人计较”宽自己的心。说笑话更是笨得像猪,一个段子没说到一半,自己就笑翻了,让别人一脸懵圈。
人是要有趣的。有趣要求智慧、阅历、修养、生命的广度和深度。能让人开心的人是智力优越的人。有趣不是强有趣、装有趣、秀有趣,更不是把肉麻当有趣,把吹嘘当有趣,把故意自贬当有趣,把恶搞、恶俗、恶心当有趣。总之,有趣不是“巧言令色,鲜矣仁”。
我接受教训,老实做名嘴们的粉丝。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记下来。下面这个故事就是军队作家袁厚春讲的——
小张乙找了个女朋友,叫丁丁。小张乙喜欢得不得了,向她发誓:“今后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刀山敢上,火海敢下,只要你高兴!”
丁丁说:“真的?”
小张乙一拍胸口:“说话不算数是小狗。你随时可以考验。”
两个人说笑着,去了电影院。
电影开映,放映的光线穿过黑暗。光柱下,小张乙和丁丁的前面一排坐着一个秃顶。
丁丁忽然靠过来,对小张乙说:“你发过誓的,我说干啥你就干啥,不会反悔吧?”
小张乙说:“怎么可能!”
丁丁说:“那好,你照那个秃顶给一巴掌。”
小张乙一怔,有些犹豫:“这玩笑怕过分了。”
丁丁一噘嘴:“我就晓得你说话不算数的。”
小张乙急了:“谁说的?”
说完就伸出手,拍了前面那秃顶一掌。
秃顶受惊,猛然回头,黑暗中看不清他的怒容,但可以听到很粗重的怒气。
小张乙很亲切地打招呼:“老曹你好,你也来看电影?”
秃顶不便发作,很不高兴地回答:“你认错人了。”
小张乙连忙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秃顶于是安静。
一场差一点闹起的纠纷,总算避免,小张乙用脚碰一下丁丁,很是得意。丁丁点头,表示满意。小张乙以为通过了考验。不料电影结束前,丁丁再次说:“你能不能再给那秃顶一巴掌?”
小张乙嗫喏:“这怎么可以呢……”
丁丁马上打断他:“算了。我晓得你就那点德行。”
小张乙一咬牙:“你小看人!”
说着就抬起手又向前面的秃顶拍了一掌。
秃顶这一次的愤怒是可以想象的。他从座位上一下蹿起来,回转身,猛扑小张乙。
小张乙不慌不忙,一面伸手挡住秃顶,一面用研究的口气很疑惑地说:“你怎么能不是老曹呢?你就是我对面办公楼的老曹嘛,为什么不承认呢?”
“谁不承认?”秃顶压着嗓子发怒,狠狠地从胸前抽出身份证,“你仔细看看,我到底是不是你说的老曹?”
小张乙借银幕的光认真审视了好久,才把身份证归还秃顶,一边嘟囔:“真像,太像了,真是奇迹。”
秃顶很不屑地“嗤”了一声,再次谅解了小张乙。
电影散场,小张乙一身轻松,对丁丁吹嘘:“怎么样,相信我了吧?”
没想到丁丁却说:“急什么,没完呢,你能再给他一巴掌吗?”
这时候,他们已经走到电影院外面,秃顶就站在他们身前的下一层台阶上。通明的灯光下,秃顶闪闪发亮。
小张乙的脸一下拉得像长长的苦瓜:“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丁丁冷冷地哼了一声,就要走开。
小张乙一把拉住:“别走,我听你的!”接着就向前面那倒霉的秃顶拍了第三巴掌。
秃顶这一次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跟小张乙拼命了。
小张乙却欢天喜地地叫起来:“老曹哇老曹,你原来站在这里,刚才在里边我没认清,拍了别人两巴掌。”
这故事很生活化,但很有道理:世界上没有不可化解的难题,问题在于你是否具备足够的智慧。
后来上海《故事会》约稿,我把这故事稍加编辑交差,标题:《老曹你好》。
作家留言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作协为了便于全国各地的作家去特区采访、写作,在深圳西丽湖建了个写作基地。我在那里住过几天,没有写作成绩,但从留言簿上看到了许多心仪已久的作家的风采。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徐迟老师的留言,只有四个字:稀里糊涂。
太妙了!既谐音“西丽湖图”,又表达了一位内地老作家对特区日新月异变化应接不暇的感受。初中就在图书馆读到徐老的诗作《撒尼人》,很是喜欢,一些明白如话的句子,把一个民族的美好表现得那么生动多彩——
云南的撒尼人人口不多,/他们可有两万多音乐家,/他们有两万多舞蹈家,/还有两万多个诗人!/还有两万多个农民,/还有两万多个牧羊人,/但不要以为他们有十万人众,/他们只有两万多人。
从那时的诗到现在的留言,快三十年过去,诗人的心还是那么年轻。
这是作家留言的一个成功例子。